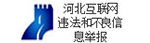9月11日,海淀火器营某小区,23岁的杜氏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患者曹兆昱坐在轮椅上。摄影/记者 李木易

曹兆昱每天早晚都要坐着轮椅到昆玉河边。摄影/记者 李木易

朝阳区西坝河东里小区家中,父亲在准备洋洋早晨服的中药丸。摄影/记者 李木易

早晨上学前,洋洋在用器械锻炼腿部肌肉。摄影/记者 李木易
每天早晨7点半,爸爸会扶着洋洋出门上学,阳光斜斜地照在他一跛一跛的腿上,泛着暖色。
洋洋自小被检查出一种称为杜氏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简称DMD)的罕见病,随着年龄的增长,行动能力会逐渐退化。在中国,像洋洋一样的孩子约7万人,对抗病痛、顽强求学、为了更好地活着,他们的成长就像被早早剧透的电影。
DMD的病症表现可以粗略理解为“肌无力”加“渐冻症”,初期跑不快、跳不起,而后肌细胞不可抑制地萎缩坏死,失去行动能力坐上轮椅,直至呼吸肌、心肌等都失去力量。这种病至今还没有研发出特效药。
“爸爸,同学们长得好快”
生活在北京的洋洋今年10岁,出生时有黄疸,经检查发现了杜氏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简称DMD)。这是一种几乎只发生在男孩身上的隐性遗传基因缺陷,平均每3500个活产男婴中,就有一例。作为一种罕见病,全国患者大约有7万人。
“爸爸,一个假期同学们都长得好快啊。”这个学期,洋洋在朝阳师范附小上5年级了,但个头却只到同龄人的肩膀。假期里,洋洋的肌肉萎缩开始加剧,穿鞋时脚背弯曲,跛脚情况比以前严重,倒地之后腿部肌肉已经不足以支撑他靠自己站起来。
DMD的病症表现可以粗略理解为“肌无力”加“渐冻症”,初期跑不快、跳不起,而后肌细胞不可抑制地萎缩坏死,失去行动能力坐上轮椅,直至呼吸肌、心肌等都失去力量。最终,患者会在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的情形下离世。目前可查的数据显示,未经治疗的DMD患者寿命不超过20岁。
这种病至今还没有研发出特效药。从检查出DMD开始,患者需要长期服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激素对于病症的药理作用至今还未完全清楚,但已经是临床实践中效果最好的药,长期坚持服用,能延长孩子的寿命,以及3-5年的行走时间。
但同时,激素会抑制孩子的生长发育,代谢紊乱导致身体发胖,所以每个服用激素的DMD患者都个子小小、白白胖胖。为了尽可能抵消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他们需要吃更多的药以补充钙质、利尿去水肿、营养心肌……为了增强抵抗力,洋洋还从小吃蜜制中药丸。
不久前,洋洋去医院做检查,彩超结果显示,由于肌肉萎缩,他的心脏泵血功能已经低于正常标准。加上新开的药,现在,洋洋每天早晨上学前要吃将近10种药。
吃过药,洋洋自觉站上30度倾斜金属板做拉伸。为了抵抗腿部肌肉萎缩,早上要站15分钟,晚上睡前要按摩拉伸半个小时。假性肿大的小腿在微微发抖,“现在习惯了,没那么疼了”,洋洋脸上没有过多表情,拉伸是他一天最难挨的时候。
“这小孩走路一瘸一拐的。”快到校门口,送孩子上学的家长随口说着。洋洋假装什么都没听见,低头扭着身体径直走进校门。
从踉踉跄跄到失去行走能力
今年23岁的DMD患者曹兆昱回忆说,虽然这个阶段听到的嘲笑最多,但能跑能跳的小学生活,是他这辈子最快乐、最自由的一段时光了。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曹兆昱在操场上摔倒了。
腿部肌肉萎缩加剧,使曹兆昱已经不能靠自己站起来。于是,他用手扒着地,磨搓着往400米外的主席台爬。手擦出了血,新裤子也磨破了,曹兆昱够到主席台,用上肢力量把身子拉起来,站稳。
“操场上有人,甚至有我们班的人。”曹兆昱用“怨恨”两个字形容。他回到教室,抄起金属制的班级牌冲进老师办公室,被四五个同学按倒在地,用跳绳绑在椅子上。
跛脚走路被同学模仿笑话,恼羞成怒打架,每周被叫家长,成了曹兆昱小学生活的恶性循环。因为上课捣乱,曹兆昱经常到教室门口罚站,后来干脆上着课自己就跑出教室四处闲晃。
因为种种“劣迹”,曹兆昱多次被学校停课回家。“据说校长办公室墙上贴着预备开除的学生名单,第一个就是我。”
“现在已经没什么能打倒我了。”曹兆昱歪坐在电动轮椅上,双手垂放在腰间,两脚内扣搭在脚踏板上。每隔十几分钟,他要用肩膀的力量快速带动整个身子,把坐姿调整到舒服的状态。残联每年会发放新的轮椅坐垫,但因为习惯,现在这个坐垫曹兆昱已经用了好几年。
今年,曹兆昱从北京联合大学毕业。如今,他的腿部肌肉已经完全纤维化,脊柱侧弯变形,“早就放弃了站起来的希望”,用变形的手指控制电动轮椅推杆,成为他坦然接受的行走方式。但在他的回忆里,从踉踉跄跄到完全失去行走能力,一步步失望,是一片黑暗的日子。
他说,如果不是家人几次要求自己重回学校上学,现在的他可能还是那个每天在角落研究用胡椒面等工具“一招制敌”的孩子,一个活在恨和怨中的孩子。
“只要你还想,我就背你上学”
10岁左右,DMD患儿会陆续坐上轮椅。来自广东的陈斌现在清华大学读博,他的病情相对好一些,坐上轮椅的时间推迟到12岁。
“上楼还要人背。”那时,即便考试成绩年级第一,他也逃不过低年级孩子的指指点点。穿衣、洗脸、吃饭,所有微不足道的小事都需要人协助,于是,陈斌想放弃了。
“读书也没什么用,被扶着上楼已经要心理斗争很久,后来还要人背。”他说,自己没脸见同学。
那天之后,陈斌一个多星期没去上课。其实在两公里外的出租屋里,他还是会每天六点半起床,然后却坐在床上发呆、纠结。终于在中午鼓足勇气,让妈妈陪着骑自行车到校门口,然后围着学校一圈一圈转。转到下午五点放学,再跟着人流一起回家,周而复始。
妈妈不知道要怎么安慰陈斌,只能陪着。自从陈斌7岁检查出DMD,妈妈便从事业单位辞职,留在家里全职照料。陈斌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成绩全县第一,考上了全市最好的中学,因为不方便,选择了离家近的学校。下节课要换教室,陈斌提前15分钟偷偷发短信给妈妈,妈妈就立马赶到学校背着陈斌到下一个教室,然后回家。
陈斌家租的房子在没有电梯的5楼。妈妈添置了一台跑步机,每天陪着陈斌跑半个小时。跑完拉伸,晚上睡觉前按照康复师的手法按摩,一天没停过。“不要害怕,只要你还想,我就背你上学。”妈妈说。
同样作为DMD患儿的母亲,李晴有些力不从心。她和丈夫现在北京市海淀区从事IT行业,因为通勤时间长,每天都是早7点出门,晚9点回家。孩子跟洋洋同岁,却已经坐上了轮椅。此前一直找护工负责照料,因为护工离开,护理价格升高,去年,65岁的婆婆从江西老家来到北京照料孙子。
因为孩子的病情,李晴和丈夫再没出过差,错失了很多职业晋升的机会。目前,国外有相关新药临床试验,或许有可能参加,但需要较高花费和家人照顾。李晴不知道,如果特效药研发生产,但买不起,她会多责怪自己。
到现在,婆婆还不知道孙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她只觉得孙子腿上没劲儿,就要多按摩、多锻炼。有时,婆婆还逼着孩子长时间站立,用力压孩子膝盖,按得孩子直喊疼。
“多锻炼,总有一天会慢慢好起来。”婆婆坚信。
“停课回家”还是“特需学校”?
洋洋入学那年,洋洋的爸爸向学校隐瞒了孩子的病情。6岁时,洋洋的行动基本正常,他希望老师能把孩子当成普通学生,不必另眼相看。更重要的是,他隐隐有所担心。
担心来自一个比洋洋大两岁的DMD患儿,轩轩。2013年夏天,轩轩通过了一所普通公立小学的入学考试,同时也在入学体检中发现了DMD基因缺陷。等到开学,家人发现孩子没有被录取。校方解释称,信息录入时不小心把孩子名字漏了。轩轩爸爸不知道要不要相信这个解释,最终把孩子送进了私立学校。
即便顺利入了学,学校建议休学的例子也偶有发生。
“家长们基本能理解学校的顾虑。”洋洋爸爸说,一个一碰就倒的孩子,就是一个安全隐患,无论学校还是家长,担心不可避免。为了让孩子留下来,有家长与学校协商签订免责协议,孩子在学校因身体原因受伤均与学校无关。
洋洋爸爸只跟老师说,孩子腿部肌肉发育不太好,尽量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但小学生跳绳是体育课期末必测项目,半年后,孩子的病瞒不住了,没办法,洋洋爸爸把诊断证明拿到了老师面前。
要不然去特殊学校?几乎每个DMD患儿家长的脑海中都出现过这个想法。但目前特殊学校大都以视力、听力、智力三类为主,DMD患儿除了行动不便,视、听、智力与常人几乎无异。
于是,有家长尝试创建面向DMD儿童的学校。轩轩所在的私立学校采用的是一种在国内较新的教育模式,文化课教学节奏缓慢,音乐、园艺等技艺类课程占比较高,通过建立一个不同于分数的评价标准让学生重新审视自身价值。轩轩父母觉得,这对于有过心理创伤的孩子们来说十分合适。2014年,轩轩父母拿出十几万元,联系朋友在北京市昌平区为DMD患儿专门创建了一所学校。
轩轩父母称之为“特需学校”。不同于义务教育,特需学校的学费是个不小的压力。尽管一再压缩,每年5万的学费还是让很多家长难以承担。有学生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就申请在学校做兼职,用劳力抵偿部分费用。
学校开办后规模不大,总共招收了十几个学生。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其中绝大多数孩子是智力障碍和自闭症儿童。“家长还是希望孩子能享受正常的教育环境,在可能的情况下多与社会接触。”轩轩爸爸说,由于缺少相关办学资质,前段时间,特需学校已被要求停课,回家的学生中,DMD患儿只剩下一个。
梦一样的毕业典礼
当年让陈斌重回学校的是学校辅导员的话。在陈斌徘徊在校门口的第11天,学校辅导员偶然间看到了他,并在放学后跟着陈斌回了家,“只记得老师说不用怕,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如今,陈斌回忆起14年前这段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的笑,“很温暖”。
幸运的是,洋洋爸爸担心的事情也没有发生。
洋洋的老师在得知孩子的病情后,帮忙开了体育课免修,开始每周定时跟家长沟通。校长偶然看到洋洋双手扒住栏杆扭着身子爬楼梯,向班主任询问了情况,四年级需要到3层时,特意让洋洋所在班级搬到了1层。今年,整个年级组没有按照惯例搬到另一栋教学楼的高层,而是全部留在了1层。
但是,教育不止于照顾。
洋洋像所有这个年纪的男孩子一样顽皮。或许是因为长期服用激素,洋洋上课常常不可控地起立,然后围着教室转圈;因为肌肉力量不足,洋洋拿笔困难,课上练习题和课下作业做得特别慢;或许出于自我保护,跟同学发生争执碰到自己时,洋洋会本能地大声喊叫,跌倒在地。
有次洋洋跟同学发生矛盾,了解状况后,当时的班主任王芳给他讲了“狼来了”的故事。王芳说,班级一直强调尊重差异,洋洋需要行动上的照顾,但更需要心理上的平等对待。“不要因为自己的身体情况自卑或自暴自弃,也不能产生弱者心理,处处寻求特殊对待。”
这个学期,洋洋爸爸收到了班主任的短信——数学课上,洋洋十分专注地听完了整堂课,练习题也按时在下课前完成,数学老师说,这是洋洋表现最好的一次。
曹兆昱的改变是在小学五年级,新换的语文老师夸他作文写得好。“那时老师偷偷跟我说,以后不喜欢的课,可以不上,教学楼走廊上摆的图书可以随意借阅。”
没过多久,语文老师在课上把曹兆昱的作文当作范文读,受到鼓励的他甚至把爸爸的初中语文课本翻出来,把课文全背了一遍。渐渐地,曹兆昱开始愿意坐下来认真听课,成绩逐渐提高,同学们也开始愿意跟他交流,曹兆昱从爱打架的“破坏王”变成了励志故事。
小学毕业典礼上,曹兆昱拄着雨伞,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演讲,“曾经在校长开除名单首位的人,竟然站在了台上。”回忆那一刻,曹兆昱说,到现在都觉得梦幻。
偶然的幸运,一个接着一个。
“如果不上学,我不敢想象”
“其实对我来说,一直念书是不断失望的过程。”曹兆昱说,高中生物课上,他知道了什么叫基因缺陷;通过网络检索,他知道了至今还没有根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十六七岁的患者腿部肌肉纤维化已经不可逆,他再没有治愈的可能了。
“但如果不上学,一直呆在家里,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我也不敢想象。”
近期,国际上发现意大利有一款用于癌症治疗的药物,或许对DMD病情有缓解,准备进行临床试验。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副主任医师戴毅了解到国内有类似的上市药物,准备也在国内做进一步临床研究。国外DMD基因治疗药物即将进入最后一期临床试验,国内治疗经验逐渐积累,标准激素治疗配合辅助器械,患者寿命有望延长到35岁。“说不定下一秒,在世界某个角落,特效药就研制成功了。”曹兆昱笑着说。
他想为自己设计一副外骨骼,帮助自己重新站起来。于是,理科偏弱的曹兆昱在大学选择学习计算机编程。外骨骼的梦想没有实现,但利用自己的专业,曹兆昱设计了一个远程教育网站。他知道,因为各种现实的困难,在DMD这个群体中,像他一样能够幸运地读到大学的人并不多。“即便无法出门,这个群体也需要学习和工作,自食其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基于这个网站,今年夏天,曹兆昱和陈斌等几位病友合作启动了名为“泛罕见病及行动受限者的成长陪伴教育项目”,并以该项目参加了北京文化创意大赛。DMD患者不仅需要通识教育,还需要职业教育,类似平面设计、动画制作、视频剪辑、新媒体运营等,都是适合他们参与的工作。目前,北京至爱杜氏肌营养不良关爱中心已经在与教育培训企业联络合作,希望把相关课程链接到这个网站中。
曹兆昱坐在卧室里,描绘着自己的计划,眼里放着光。桌子上相片,是小学时还未坐上轮椅的自己,身旁是最爱玩的滑板车,跑不动的时候,骑上车能让他感受到速度带来的自由。
他的同伴陈斌说:“每个人的自由都有一个规界,在这个框架内,我们可以做任何事,也就是说,我们拥有绝对自由。”
傍晚,洋洋放学回家,5岁的妹妹跑过来,缠着哥哥陪她读新买的绘本。2014年,妹妹出生,洋洋又多了一个陪伴。平时,父母刻意培养洋洋的阅读习惯,四五岁时学儿童画、今年开始学习素描,将来还计划学国际象棋。
“未来即使坐上轮椅,我也希望他能做些事情。”洋洋的爸爸说。(文中洋洋、轩轩、李晴均为化名)(记者 马瑾倩 姚远 李木易 应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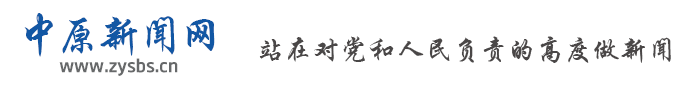
 0310-3111082
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30477986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