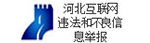黄若依(左一)在顺庆公安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黄若依穿汉服的背景。她至今没有一张正面全身照。受访者供图
黄若依不是黄若依。或者说,这个名字原本不属于她。
她出生时,父母给起的名字叫黄媛媛。只不过,没有任何文件能够在法律上证明这个名字的存在。她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证,在人生的前24年里,她一直是一名“黑户”。
由于父母没有结婚证,且超生,她出生时没有落户。后来,办理户口登记时,按规定需要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可是,母亲失联,父亲不配合做亲子鉴定,“黑户”问题就这样一直困扰着她。
即使是她亲近的朋友,也很难想象,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她无法正常办电话卡、无法坐火车、不能去正规医院看病、不能谈婚论嫁。
这个问题,直到今年9月22日,在她求助媒体后才得到解决。在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分局办理户口登记那天,她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黄若依”。
办理户口以后,她需要迎接的,远不止那个新的名字。10月30日,黄若依来到南充市教育局,想知道是否可以重新接受义务教育——没有户口的日子里,她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拿到身份证后的这1个月,黄若依报名了驾照的科目一考试,去医院看了眼科。她7岁前被寄养在姨婆家,总是挨打,落下了斜视的毛病,小时候总被人说是“斗鸡眼”。虽然她早就原谅了姨婆,但她在意这一点缺陷,为此她没有拍过一张全身照,只让别人拍她的背影。
没有户口的时候,她没法去正规医院看病,如今她希望能够把眼睛治好。她想要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1
在办理户口登记之前,黄若依的名字、工作换来换去,恋爱谈过几次,但无疾而终。
她先后在奶茶店、咖啡馆、超市、理发店打过工,还曾在夜市摆摊,这些工作对身份证检查不严格。在咖啡馆打工时,她被人叫做“小凤”。她总是应声很慢,因为那来自她借用的身份证。黄若依的朋友张宣说,因为怕被人发现冒用身份证,她每个工作最多做两个月。
今年的疫情让她在城市里受到的限制又加上了一环——她的微信是托张宣进行的实名验证,健康码也要用他的。她借用的身份证在2019年到期,这意味着今年她彻底不能坐火车了。
从2016年开始,张宣两次陪着黄若依去派出所咨询户口问题,但都绕不开“把你的父母叫来”。这成了黄若依落户过程中越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她无法提供《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根据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她需要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来办理户口。当地一个派出所所长曾告诉她,“不拿鉴定你到我这来也没有用,我也没有权力去执行。”
但是,黄若依的父亲和母亲分居后,始终把她看作“归母亲管”的孩子,不愿意惹上麻烦,要求黄若依先拿出2万元才配合落户。这笔钱后来涨到了5万元、6.6万元。黄若依曾经把做亲子鉴定的人带到了父亲面前,父亲不愿意伸手配合采血。
黄若依开始寻求法律和媒体的帮助。她来到妇联时,工作人员说,本可以帮她找法律援助,但她没有身份信息,没法开推荐信。黄若依去找了律师,想咨询能否起诉父亲,强制要求他配合。律师说,由于她没有身份信息,不能立案。
最后,黄若依来到报刊亭,到报纸上去找记者的联系方式。
9月16日,《南充晚报》根据她的叙述刊发了报道,随后有警察给她打了电话,说他们看了报纸,很快会为她办理。9月22日,黄若依拿到了临时身份证。
拿到身份证后,黄若依首先想到的是上学的问题。
她没有上过学。她可以在微信上打出大段的文字消息,但提笔写字对她来说很困难,“要照着写才行”,“乘法口诀”也不太会背。朋友刘妙说,以前自己去上学的时候,黄若依就无处可去了。“她认识的字都是自学的,自己看书学的。”黄若依的母亲教会了她拼音,而电视成了她重要的老师,“从少儿频道里学到很多东西”。
现在,黄若依住的地方有一个两层的书架,上面摆放着十几本书,有《逻辑思维训练1000题》《每天健康一点点》,还有一套小学语文的教材,书脊上写着,“义务教育教科书”。
“义务教育”这个概念,近几年她才明白。过去,她一直以为不能读书,是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有钱人家孩子才能去学校上学”,因此,她几乎从未在母亲面前问起读书的事。
黄若依说,她童年时对未来的职业也曾有很多幻想。她曾经觉得“做警察真好”,还想过成为国家级运动员。但是,没有上学,这些都无从谈起。
9岁时,她有一天抱着一本书去南充市的一所乡村小学找邻居姐姐,就在窗边站着。一个老师看见了她,以为她是某个班级上的学生。黄若依告诉她,自己不上学,哪个班的都不是。老师说,你把你妈妈叫来,不收学费,只给书本费就好。经过一番劝说,妈妈同意她去那个学校旁听三年级的课程,但没有学籍。
很快她们又搬家了,学校生活只持续了3个月左右。
10月30日,她来到南充市教育局,了解是否能重新接受义务教育。教育局工作人员说,这么大年纪的学生没有学校收。他们建议她可以去试试职中,但是职中也没有义务接收她。
黄若依理解教育局的意思,“是当时的监护人给我造成这样的后果,就是说国家没有一定的义务去弥补。”但黄若依觉得,“小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思考这些问题,而且我从12岁左右,就没有人一直带我,完全是自己长大的”。
离开教育局,黄若依又来到自己曾经旁听过的那所学校,想看“能否接收我这么一个特殊的学生”。副校长说,听说过她的故事,感觉很同情,但是她的年龄比较尴尬,很难单独规划出来一个教师来教。“这么大的人,来上学也会很奇怪”,学生和其他家长都会有看法。
小学无法接收,她又去职中咨询。11月2日,黄若依来到四川省南充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老师说,没有学籍不能收,但是由于她情况特殊,可以去问问教育局能否出示一个什么证明,这样他们有可能会收。
尽管在朋友吴青云看来,重返校园并不现实,但黄若依自己倒向往那样“枯燥”的生活。“拥有的人不会去珍惜”,她想住在封闭式学校里面,只有周末可以出来,按时睡觉起床,“在学校里面你除了学习什么也不能干”。她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得到调整。除此之外,她觉得以现在的文化程度,她只能选择工资不太高的工作。
2
小时候,黄若依并没有感受到“黑户”带来的影响。她常去的黑网吧、商场、书店不需要出示证件,身边的玩伴也都是未成年人,都尚未拥有身份证。“我当时没觉得我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
2013年,17岁的黄若依在江苏打工时被要求提交身份证。辗转找到父亲,她这才发现,家里的户口本上没有自己。“纸包不住火”,对公司推脱了几次“身份证正在办理”后,黄若依离开了那个岗位,回到南充老家。
黄若依记事起,她父母已分居,她随母亲生活,但12岁时母亲和她失联。找不到父母,为了谋生,黄若依只能借朋友的身份证在本地租房和找工作。
黄若依说看到别人家人团聚,她觉得“只有我是一个人”。甚至看到恋爱的情侣,她都想到“我没有身份证,不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2019年,黄若依曾和前男友走到了谈婚论嫁的节点上。男方父母隐晦地说,“要先把户口问题解决了”,男友没有站出来维护她。他们很快分手了。
因为没有身份证,她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小时玩伴徐晴告诉记者,“她以前没有身份证,条件特别不好的黑宾馆才会收她。”张宣还把家里的房间腾出来给她住过一段。
她用着借来的身份证,照片上的人和她并不相像,她总解释会说,“瘦了,所以样子有变化”“化妆了”。但她还是“提心吊胆,像过街老鼠”。“如果被发现了,我也就实话实说,这不是我想的,我没办法。”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采访时,黄若依的父亲黄大前说,黄若依在家排行老三,当时上户口需要交罚款,他们拿不出来这个钱。现在他也不是存心阻挠,只是觉得,家里有些事还没有说清,这个女儿应该是归母亲管,担心以后她母亲回来,产生纠纷。他还说,钱是帮她母亲存的赡养费。
黄若依的母亲姓名不详,黄若依说,可能叫“王巧”或“王宗巧”。她是陕西安康人,高中学历。根据黄若依的说法,她20岁时被外公赶出家门,来到广州打工,遇上了当时30岁的黄大前,后来随他来到四川西充县。按照黄若依和其父亲的说法,黄若依母亲有些精神上的问题,她曾见过母亲在烟盒、旧报纸、广告页上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贴满出租屋的墙。
徐晴还记得她最后一次见到黄若依母亲的场景:在“黑宾馆”里一个非常破旧的房间,黄若依的母亲问12岁的黄若依有没有钱,黄若依给了她100元。她母亲当时似乎要退房离开。
那100元是黄若依在电玩城里用游戏币一点点换来的。黄若依回忆,母亲经常消失一两天、三四天,最后彻底失联了。网吧、电玩城成了她童年的避风港。
“她相当于是自己养活自己”,当时读三年级的徐晴家住那个网吧附近,她在这里认识了黄若依。黄若依和她一样大,但却和他们不一样,“又瘦又小,精神状态一点都不好”。她回忆,当时小区里的大人会当着黄若依的面说她像“吸毒”的人。黄若依往往就默默听着,也不反驳。
徐晴说,黄若依几乎靠在电玩城里赢钱为生:用游戏币换钱,一天赚几元,或者十几元,“有钱就有饭吃,没钱就不吃”。后来网吧的阿姨看她挺可怜,让她在那里当了个小网管,一个月给她几百元。刘妙还听说,黄若依有时候饿了或是渴了,就去百货大楼,要免费的水,或者吃一些免费品尝的东西。
黄若依说,和母亲在南通顺庆生活的5年中,他们差不多隔两个月就要搬家。她从来没上过学,但是,妈妈会把她打扮得跟普通的小朋友一样,周一到周五让她背个书包出去,里面装个本子和笔,别人放学的时候才能回家。这种生活至少持续了两年。
她背着书包在城市里游荡,最常去的是五星花园附近的商场、肯德基、德克士,在那里参加小朋友的活动,赢礼品,也在那里看电视。张宣说,她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我们没去过的地方,她全都去过”。黄若依回忆,她有时候会找一个人少的地下通道,坐在台阶上拿着书看。路人问她“为什么不去上学?”,她往往默不作答。
吴青云是黄若依18岁左右在动漫展览上认识的朋友,刚见她时,吴青云觉得,“从来没见过这么瘦的女孩”。
她会攒钱买一套动漫服装,穿到动漫展览上去。角色扮演成了黄若依后来最大的兴趣。“你扮演着自己喜欢的角色,会有别人也喜欢这个角色,可能会以这种方式来博得一种关注,就感觉你就会有朋友了。”
3
刘妙是黄若依十几岁时的玩伴,最初听她说起身份证的事,觉得“办身份证不是很简单吗?”“对于我们这种有身份证的人来说,怎么会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身份证的人呢?”。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黑户”有1300万人左右,占总人口1%。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这份意见提到,“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
很多“黑户”在这份意见指导下成功落户。但黄若依并没有因此走出死循环。
在家庭和有关部门两边,黄若依一直徘徊等待了7年,直到把这件事“闹大”,见诸报端。2020年9月22日,在见报5天后,若依拿到了自己的临时身份证。父亲始终没有配合。
徐晴说,抛开家庭环境不谈,如果能有一个户口,黄若依这些年至少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段稳定的爱情。
尽管黄若依比张宣要小,但张宣记忆中,黄若依一直是一个强势的大姐姐,会带着他玩,教他道理。吴青云也说,她很讲义气、果断,有时候还特别固执,认死理,认准了什么事情就必须要执行。
而在徐晴的眼里,这是她的一种“伪装”。她很少把那些难过的事跟朋友说。“明明其实我感觉她挺难过的,却一定要跟我说没事。”徐晴说。
张宣也回忆起她柔软和脆弱的一面,那是2009年,她看到黄若依在网吧里,总是怀抱着一只狗不放手。
黄若依说,12岁时,她在网吧玩QQ炫舞,在游戏里面加了一个好友,认了那个好友做哥哥。有天,她发现他偷了她游戏里的物品,觉得这个人没有真的把自己当妹妹。她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处境,“没有谁能那么在乎你。我妈也不管我,我爸爸和姐姐那个时候不知道在哪儿。”
上户口的时候,她下决心要用一个全新的名字。“别人都说,名字是要父母取才行,父母是爱孩子的,会精心为孩子取下名字,但是我没觉得他们多爱我,所以我想给自己取个好听的名字。”如今叫黄若依的那个女孩儿说。
黄若依觉得,24岁拿到户口,还不算太晚。“就像很多大学生毕业的时候,是他们人生真正刚开始的时候。那现在我去做任何事,去学习,去考驾照,都还不算晚。”
实习生 郭玉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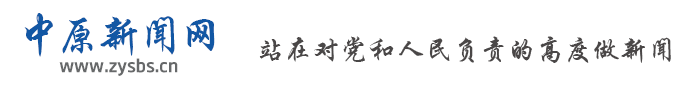
 0310-3111082
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30477986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