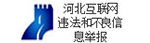何炯在宣讲会上给听众科普器官捐献 见习记者 陈馨懿 摄
她是器官捐献协调员,奔走于生死之间
即使看多了生死,她常常也会忍不住流泪,因为——
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诉说
46岁的何炯,似乎很难逃离“悲悲戚戚”的工作。
20年的护士生涯,她一直在浙医二院重症监护室,工作常态就是生命的脆弱和无助。
38岁的那年,她调离护士岗位,成了省红十字会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份陌生的职业。直白点说,就是针对临床上确认脑死亡的病人,劝说其家属捐献病人的人体器官。太过冰冷和残忍的这份工作,何炯更愿意诠释为“生命摆渡人”:拯救一个生命,延续一个灵魂。
认识何炯,源于最近杭州本地论坛上一则讨论器官捐献的帖子。发帖的姑娘和父母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器官捐献,对一方意味着死,对另一方又意味着生,抱歉、卑微、感激、幸运……人世间似乎没有哪一个决定让人如此纠结。
8年时间,何炯和同事们劝说了四五百个家庭,成功的有一百多例,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其间遭遇冷眼和不理解,甚至谩骂。
“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诉说。”何炯将这些故事装在心里。
因为你能做这个工作
躺在病床上的那些青年与中年,往往因为一场意外或一次突发疾病,让他们基本符合临床脑死亡的标准:比植物人更糟,没有恢复的可能,不再有自主呼吸。
和真正的死亡,只有一台呼吸机的距离。
拔掉呼吸机,不用太久,他们的心脏就不再跳动,血液也停止流动。再过五分钟,没有取出的器官就会冷却凝固。
每凝固一个器官,就意味着平均一百五十位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失去一次机会。心、肝、肾衰竭的患者,根本来不及让希望变成失望,因为等候列表里,新的病人进来,旧的病人已经离世。
但如果捐献器官,一条生命,至少能拯救另外三条生命,让三个家庭重燃希望。
这些信息都在何炯的心里。
有过20年重症监护护士的工作经验,做过浙江第一例肝移植特护,这些都是她如今成为协调员的优势。
但即便如此,她依然很难在开始介入时单刀直入介绍器官捐献的种种好处。
懂得换位思考,这也许就是她在2012年,被选中为浙医二院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原因吧。
“只有你能干这个工作。”就是这么一句话,何炯上岗了。
她知道这个工作难,却不知道有这么难。
器官捐献,实行直系亲属一致同意的一票否决制。即使到捐献前的最后一刻,都可以反悔。为了照顾家属心情,何炯不会刻意穿工作服挂上证件,普通得就像穿着严肃的围观者。
“你好,我是红十字会的协调员。”这是见到家属时,何炯的开场白。她故意省略了“器官捐献”四个字。因为她知道,这个词有时候比“死亡”还要敏感。
正因为敏感,所以每一个措辞,每一个停顿,她都很谨慎。
何炯说自己是幸运的,遇到的家属都挺温和,只是“温和”的背后是坚决的反对。
在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思维中,完整即是圆满。大部分家属也有这样的理解:“器官都捐了,还能拼凑来生吗?”这成为了何炯工作最大的障碍。
2010年至今,浙江省有将近1500个器官捐献案例,生前表达过意愿的只有二三十人。
而劝说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每一次在和家属见面之前,何炯都要预演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人与人的沟通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套,非要说的话,要让家属知道我是来帮助他们的,而不是来索取的。”
他/她有知情的权利
“我努力了,但我不强求”是何炯做协调员的心态。她坚持任何事情都应该在平等又真诚的环境下被促成。
在劝说过程中,她都尽量放低音量,柔声细语。“你们有没有想过患者去世以后怎么办?”这是她用来引入话题的一句话,大多数人都没有准备好亲人的突然离世,“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可以听听看。”
介绍完器官捐献,何炯会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思考,不会死缠烂打。
克制很重要,要让家属自己做决定。曾经有家属捐献了又后悔,抱怨要不是协调员一直跟着自己,他们怎么会心软答应。“我要是听到家属这么说,我会很难过的。”
她当然希望,人体器官捐献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多,只是有些意外不能避免。
曾经,一个女人遭遇车祸,兄弟姐妹和子女都同意了器官捐献,却向年迈的母亲隐瞒了这个消息,老年丧女,没有人能承受。家属提出代签,但何炯拒绝了,“虽然很可惜,但老母亲有知情的权利。”
一天行驶800公里只为跟家属见上一面,这么多年都不敢出远门因为要24小时待命,不敢穿颜色太鲜艳的服装会影响家属的心情,给予家属工作之外的私人帮助……这些,都是协调员的日常。从业8年,原本就感性的何炯,似乎变得更容易流泪了。
“即使看多了生死,常常也会忍不住,情感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我想听他叫我一声“爸爸”
一般来说,为了避免被情感左右判断和行事,协调员不和受助者接触。
8年来,只有一次,何炯无意间打破过“零接触”。
她在病房里碰到了那位年轻的受助者。一米八的大高个,三十来岁,很帅气,因为心脏衰竭无法躺着入眠,需要打针才能坐靠着眯会儿。是否还能等待到一颗健康心脏,他不知道。
何炯目睹着这一切,心里很难受。
她心理建设了一阵,还是下定决心,再次联系了各项指标都比较匹配的捐赠者的家属。捐赠者是一个因意外而过世的女生,父亲和哥哥已经同意捐赠女孩的肾脏、肝脏和眼角膜了,但是心脏除外。
“受助者是一个丈夫,一个爸爸,一个儿子。一颗心脏,救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他的一个家。”何炯说得真诚,最后打动了那位女生的父亲。
这是何炯第一次为了受助者而“努力纠缠”。幸好,结果如双方所愿。
但女生的父亲有一个条件:“我想听他叫我一声‘爸爸’。”
多无力又动人的要求,何炯没有理由拒绝。
心脏移植手术之后,何炯来到了受助者的病房,拨通了电话,两个陌生男人,因为那一声“爸爸”,联系在了一起。
何炯并不知道电话那头,女生的父亲是否泣不成声,但她知道那一声,弥补了遗憾。(本报记者 杨茜 见习记者 陈馨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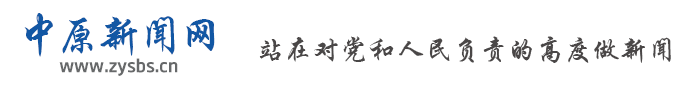
 0310-3111082
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30477986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