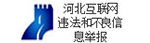冯娜和学生一起跳竹竿舞。受访者供图
眼前这个乡镇,没有像样的硬化路、没有商店。
这里有雨后满地爬的小黑虫、手指长的蟑螂、在屋里乱窜的老鼠;有一条土路通往县城,还有一群初中生,等着刚从大学走出来的老师。
去年8月初,姬杨第一次来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鲁容乡,眼前的景象令他吃惊。这个土生土长的贵州年轻人没想到,在距贵阳3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居然还有这么贫穷的乡镇。
姬杨记得,“当时全乡只有3个单位:乡政府、医院和鲁容中学”,要买东西只能去县城或临近的乡镇。而这就是他和研究生支教团的4名女生要生活一年的地方。
贵州大学的本科生大部分来自贵州省内,贵大研支团的成员中,贵州人也常常占半数以上。十几年来,每年都有数名贵州大学的准硕士生留在贵州最基层支教,花一年的时间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
小班主任的故事
听到校长在大喇叭里宣布“七(一)班班主任为王斐”时,王斐并没在意。
此前几天,他和另外4名研支团同学第一次来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兴仁中学,预备开始2018-2019学年的支教生活。王斐报名成为英语教师,他将要承担两个班的教学任务。
当天下午,王斐去打听第二天的上课情况,才听说自己是班主任——他可是个教学经验几乎为零的新手。
王斐曾以为当教师很简单:“一天两节课,一节课45分钟,一天就上90分钟的课,多轻松啊。”等他走上讲台并接手班主任工作,才发现过去的想法是多么不现实: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1点睡觉,他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刚接手七(一)班时,“班里鸡飞狗跳,每天感觉房顶都快被掀翻了”,其他任课教师也经常找他告状。就连中午休息时间也不得安宁:宿管打电话说两个学生打架了,学校老师打电话说某某同学又调皮了……第一个学期,他一天午觉也没睡过。
为了快点“入门”,王斐跑到图书馆看《班主任秘笈》、向老教师请教、给了解青少年心理的专业教师打电话……
王斐过了一个月才意识到自己用错了方法。一开始,他跟学生相处时很和气,总是用商量的语气跟他们说话,和气的后果就是:学生觉得他好欺负。
王斐意识到问题后就“变了脸”,“每天装作很严厉的样子”。早上学生还没到校,他就坐在教室,看谁迟到了;哪个学生没完成作业,他就陪着写作业,直到学生写完为止;每天晚上查寝、数人数,所有学生都睡下了,他才去休息。
如果学生生病,不管多晚他也会送去医院。那段时间,王斐的目标就是“努力让他们又尊敬我,又喜欢我”。
作为新班主任,王斐还遇到了令所有老师都头疼的学生。政教主任告诉他,从小学升上来“四大金刚”,其中一名就在王斐班上。
“金刚”名不虚传,他顶撞年轻老师,抢同学橡皮,一言不合就动手。虽然年轻的王斐能管得住这个孩子,但无法走进他的内心。
有一次,王斐听说他被咬了,情况有些严重。王斐去了校医院,却发现人不见了。王斐急得在学校找了两圈也没找到,后来在操场的一个角落找到了他。
当时,这个学生带着哭腔诉说着什么,周围还围了一圈男生。这是王斐第一次看到他哭。
王斐叫走了其他的男生,陪他在篮球架下坐着。“他说这个时候特别想妈妈。”王斐这才知道,孩子来自单亲家庭,妈妈已离开他多年,爸爸在外打工。
王斐送他回了家,那是一座建在镇上的二层砖楼,孩子平时独自住在二楼。楼房没有粉刷,砖块裸露在外。这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每天一个人做饭、吃饭、洗衣服。“那时我才知道,他的表现跟他的家庭有那么大的关系。”
那次长谈之后,孩子再也没惹过事。他有次去山里玩,还给王斐带回一根庙里的红绳。
作为贵州大学研支团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班主任教师,王斐那一年有很多艰辛,但他从没哭过。可是离开的前一天,王斐和研支团另一名男生,也是和他搭班的数学老师,坐在教室的台阶上哭了半个小时。
课堂外的努力
王斐离开后,冯娜和4名研支团同学走进同一所学校。冯娜的教学任务相对轻松——教两个班的道德与法制课。
在这个有上千名学生的乡镇中学,90%的学生住校。开学不久冯娜就发现,学校的大热水炉坏了3年,只有食堂有一个小热水炉。热水供应不足,不少学生冬天也用冷水洗头洗澡。
研支团的同学做过预算,换一个新炉需要6.8万元,烧一次热水可以供应几百人。但对缺乏收入来源的研支团学生来说,这无疑是笔巨款。
冯娜记得,她从9月中旬开始尝试联系捐赠,每天给慈善机构发微博私信、发邮件,连续发了两个月,全都石沉大海。其间,遵义一家公司愿意以成本价为他们提供设备,所需资金降到4万多元。但就连这笔钱他们也无力支付。
11月初的一天,一个归属地为北京的陌生号码来电,对方自称是某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她的求助信息。冯娜没想到自己发出的信息竟然真的有了回应。这家公益基金会发起了募捐,不到10个小时就凑够了4万多元。
事实上,学校存在的硬件困难不只这一个。冯娜了解到,丹寨县的自来水中钙离子含量高,需要净化才能喝,不然容易导致结石。“自来水管流出来的水是黄色的,捧在手里都能看到泥沙。”她说。
支教的末期,冯娜用相当一部分精力来争取赞助。很多公益组织有专门的帮扶方向,冯娜终于找到一家专门赞助净暖水设备的机构。“支教结束前一个月,神经都绷紧了,就想把收尾工作做好。捐资助学很艰辛,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这一学年,冯娜和伙伴为丹寨县的中小学共募集了42万元,另一支支教团队为贞丰县的学校募集了70多万元。
另一场考验
当冯娜为了热水炉、净水器而奔波时,姬杨在贞丰县的鲁容中学面临另一场考验。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鲁容中学从校长到普通教师经常要下乡扶贫。有段时间,全校初中生的大部分教学和管理任务就落在姬杨和4名支教教师身上。
姬杨每周上20多节课,比正常工作量多一半,“教学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除此之外,他还兼着广播室、团委的工作。
一天深夜,姬杨加完班回到宿舍,他高度近视的眼睛酸痛,就想立马倒在床上。这时他突然发现深蓝色的床单上有一点黑色的东西,于是凑上去看了看,又闻了闻——那是一颗黑色的老鼠屎。“当时都要崩溃了!”姬杨说。
有些学生的表现也令他恼火不已。他们上课时喊口号,那是从短视频App上学来的。班上学生大多有智能手机,这些短视频App是学生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途径,可是姬杨发现,他们也从中学到了染发、打架,甚至看了一些色情暴力的内容。
王松是姬杨前一届的贞丰支教队队长。他到贞丰不久就意识到这里的闭塞:有的孩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还有的连鲁容乡都没出过。王松开始筹划带孩子们出去游学,激发孩子们走出去的志气,“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考出去是最便捷的路径”。
王松等人筹备了6个月,最终,在贵州省科技协会和一名在贞丰挂职的贵州大学教师帮助下,王松和研支团伙伴带80名贞丰孩子走出贞丰县,在贵州平塘看大射电望远镜,到贵州大学参观,还去了贵州省科技馆。
这些孩子当时的表现让王松至今难忘。在贵州大学图书馆时,王松告诉大家,哥哥姐姐们正在看书学习,要保持安静。这群孩子一句话也不敢说,安静地在书架间行走。
离开图书馆时,一名男孩告诉王松:“老师,有一本书今天我没看完,我以后还会再来把它看完的!”
这一年里,研支团同学还肩负着扶贫的任务。开学前,研支团是乡政府的“小助手”,资料录入、走访农户等工作都要参与。支教开始后,他们还趁为数不多的空闲时间跟乡政府的年轻干部一起走村入户。有人感叹:“这一年,看着它一天一个样。”
姬杨至今对一条扶贫标语印象深刻:“今天很艰难,明天会更难,但是一天会比一天好。”经过一年磨砺,他对未来要走的路更为笃定。
结束支教后,姬杨从土木工程专业转到旅游文化学院读研。课堂上,老师讲起农村社会的状况,“我真的太知道是什么样了”。他下定决心,“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要把它发展得更好。”(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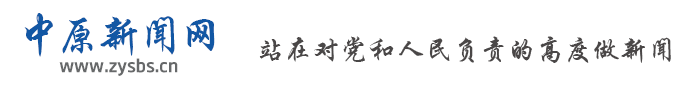
 0310-3111082
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30477986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