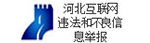训练结束后的分组总结。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马宇平/摄
“中国跳得最快的孩子”目前在广州市的乡下一所不起眼的学校里。在跳绳这个运动项目上,这个叫岑小林的孩子保持了两项世界纪录。他平均每秒能够跳7.5次,在此情况下,肉眼几乎察觉不到那根跳绳的存在。
在国际跳绳界,这所连体育器械都不完备的中国农村小学具有相当的统治力。一个月前,在挪威举行的跳绳世界杯赛上,这里走出的17个孩子,在与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竞争后,夺取了全部金牌的六分之一。自7年前推广跳绳以来,这所学校的学生改写了几项世界纪录,拿回的奖牌可以装满40多个书包。
最新一批世界冠军从挪威回国后,地方政府和商会为他们举办了庆功宴。但回到家里,岑小林没对父母讲过北欧见闻,也没提到关于比赛的任何事情。奖牌暂时由学校保管。在挪威,他刷新了一项由他创造的纪录,但在他的家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比赛那段日子,这个孩子生活中的更大变化是——他的两箱物品混在全家人的行李中,搬到了另一处出租屋里。
搬家是他所熟悉的——世界冠军们大都是随父母临时在广州郊区落脚的打工者子弟,籍贯分别在贵州、重庆、广西或湖南的村落。他们跟随父母迁徙,更换住址也更换学校,有的学生19岁才读到小学六年级。少数人能够在此地读完初中,然后像父辈一样,出去打工。他们总在迁徙。
冠军们早就适应了角色的快速转换——前一天在国外比赛,从王子或者其他大人物手中接过奖牌,转天身着印有中国国旗的领奖服出现在中国机场,接过接机人群送来的鲜花。回到花都这个盛产花卉的地方,平常日子里,他们会钻进父母劳作的花棚,去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
1
毫无疑问,体重超过100公斤的赖宣治是这支跳绳队中跳绳最差的。但他又是唯一的教练和全校唯一的体育教师。
这所名叫七星小学的学校紧挨着792乡道,每当货车、罐车和摩托车打墙外飞驰而过,尘土就会越过围墙漫进来。
2010年,24岁的赖宣治成为出现在这个校园的第一位大学生教师,结束了这所学校体育课常年由语文或数学教师代课的历史。那时,条件更加简陋。学生们跑过土操场,穿过茂盛的荔枝树、芒果树、龙眼树,进入老旧的教学楼。一个暑假的功夫,校园里的杂草就能没过小腿。

学生们在午睡。
跳绳的兴起,在这里更多是因地制宜的选择。赖宣治到来时,学校只有一块土操场。他试过在尘土飞扬中教学生们打篮球,但他们拼抢时互相撞倒,家长投诉到校长那里,投诉多了,篮球也就停了。他带学生练田径,由于器材匮乏,唯一能开展的田径项目是跑步。花都区教育局举行第一届中小学生跳绳比赛时,校长张有连带他去观摩。他们的结论是,这项运动似乎适合七星小学:不会有激烈的对抗,不需要昂贵的设施。
可是,这项运动并不适合赖宣治。即使在身材变胖之前,他也不擅长跳绳。花都区教育局2009年开始推广跳绳,对中小学体育教师定期开展跳绳达标测试,他总是倒数几名。他会找校长在病假条上签字以逃过测试。某次测试他实在逃不掉,硬着头皮去跳,补考了3次才算通过。
到了2012年,跳绳成了他躲不开的项目。广州市教育局决定将跳绳作为中小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运动技能,列入每年体育学科学业质量评价必测项目,要求学校每周安排一节体育课用于跳绳。那个学年起,赖宣治不得不向学生们传授他最不擅长的项目。七星小学组建了跳绳队,潜在的世界冠军们从镇一级的跳绳比赛开启了冠军之路。
队员是从四五年级拉来的——六年级面临毕业,低年级的孩子则太小。整个学校那时共有一百五六十名学生,赖宣治拉来了50多名,几乎“挖空”了两个年级,田径队也被合并进了跳绳队。岑小林是少有的低年级队员。他们每天在学校的榕树下训练两个小时。不少学生嫌累退出,后来,剩下的全是外地来的孩子。
经费紧张,体育教师发挥了他的想象力:旧教学楼拆除时,他从工地上找来废旧电线,去墙外砍竹竿,以竹竿为把手,在上面钻个孔,电线从里面穿过打个结,一条自制跳绳就完工了。
赖宣治介绍,连修摩托车时看到的刹车线都给过他灵感。2013年他研究跳绳到“疯魔”。他看书、研究视频、参加区里组织的跳绳培训、钻研“半蹲跳”跳法。技巧之外,剩下就是“玩儿命地训练”。
岑小林是第一批队员,目前是单人30秒单摇跳绳、3分钟单摇跳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刚进队时,他1分钟只能跳50多次。现在,他的纪录是3分钟1152次,被外国网民称为“中国跳得最快的孩子”。
2
但没有人会认为岑小林天赋异禀。“跳绳和天赋没有关系,就是练出来的。”七星小学的队员聚在一起时这么总结。
曾有体育局的教练去选苗子,想从跳绳世界冠军中选拔一些人练田径或者其他项目,都失望而去。他们的身体素质并不出众。
有队员介绍,平均每两个月,他们就会用断一根直径1毫米的钢丝绳。“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赖宣治教导学生。
“天天练,每天重复,每练一个动作重复3万次。”14岁的孔荧莹拥有十几个世界冠军头衔,她说:“天才都是练出来的。”她喜欢花样跳绳,正在试着编一套四人同步花样跳绳动作。
对这项运动,教练和队员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两人交互摇绳跳”这个项目,他们最初花了大半个月才搞明白人怎么进到绳圈,而现在,新队员3分钟就能学会。
器材室里挂着属于队员的上千根跳绳,在五颜六色的塑料把手中间,没有哪两根是同样长度的——学生凭感觉来自行调节长度。不同的绳子有不同的功用:练耐力、练花样、练速度。每人至少要用3条不同类型的绳子来提高手腕力量。
他们对鞋底特别敏感。跳绳穿的鞋鞋底不能太厚,要轻,队里新发下来的鞋子几天就被“踩得很合脚”。“鞋底前脚掌和鞋面回弯的地方最容易破,鞋底直接破了一个洞,很多双都这样。”14岁的队员陈嘉伟说。
跳绳队一日两训。每天上午从6点半训练到8点,下午从4点训练到6点。从开学之后,只有期末考试当天不需要晨训。到了假期,每天的训练时间会拉长到六七个小时。如果赶上比赛,训练强度还会增加。队员没有带毛巾的习惯,汗水快落到眼眶里时,就随手刮一下,地面很快出现一滩水。
在国内外各种大赛中,他们总是能在赛场找到空地躺下休息。这个习惯是在学校养成的:他们直接枕着软垫,席地而卧,快速进入午睡。
队员们的体能训练也很简单:蛙跳,爬楼梯,跑步,以及拉着汽车轮胎跑步。训练结束后,学生两人一组,互相踩小腿让肌肉放松。
赖宣治给每名队员都定了训练目标——都是接近同年龄段世界纪录的目标。去挪威参加比赛前,大家围坐在训练室的地上,认领了各自的参赛任务。最主要的一条是,“拿下全部速度跳绳项目的冠军”。
跳绳这项运动可以分为速度跳绳和花样跳绳两个大类。一个公认的观点是,中国人在速度跳绳上处于顶尖水平,花样跳绳略逊一筹。
在中国,跳绳是一项新兴的运动。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成立于2012年。该中心常务副秘书长、世界跳绳联盟副主席陈阳辉说,2013年,中国国家跳绳队首次参加亚洲跳绳锦标赛时,在个别速度项目上能取得好成绩,花样项目上则“非常薄弱”。现在,中国队在速度项目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花样项目的进步也很大。
但在广州的这支跳绳队,学生们练习时并不区分项目,每个人既要练习速度,也要练习花样。到2014年,学校有了跳绳的专用场地。能用到的辅助器材是绿色加厚海绵垫子。学生们不得不克服内心的恐惧,在上面学会空翻、后手翻、侧空翻,并在做出这些动作的同时确保身体穿过飞舞的绳圈。有队员练习时受过伤,后来再没做过这个动作。
正因跳绳不像篮球、足球运动那样普及,七星小学才有了露头的机会。“如果其他大学校搞,还轮得到我们吗?”赖宣治说。
他认识的一些家长并不支持孩子参加跳绳队,以至于他需要去说服这些冠军的父母,让孩子跳下去。父母们总是会问此类问题:“拿了跳绳冠军有什么好处?跳绳队对他以后有什么帮助?”一个问题备受关注:拿了冠军有没有奖金?
答案是令人失望的——没有。最重大的国际比赛也不设奖金。优胜者不会得到任何来自其他渠道的奖金。
陈阳辉说,他们正在争取将跳绳列入全国运动会的正式项目。从观众规模和商业价值来看,跳绳目前还是个小项运动。
今年去挪威参加跳绳世界杯赛,七星小学的参赛者平均每人开销在3.3万元左右。区财政拨了50万元,剩余的由学校“化缘”解决。比如,队员的行李箱上印着一家陶瓷企业的名称,一家研发材料的公司为他们提供运动鞋垫并赞助5万元,还有一家教育类企业赞助了5万元。一家贸易公司提供的赞助是几台空调,其中两台挂在跳绳训练室里。
有人从新闻里知道了这支队伍,要为学校捐一些器材,他们“高兴得不得了”。赖宣治说:“捐赠给学校两万块钱的器材,对于别的学校可能没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是大事情了,可以买50个篮球,50个足球,200根绳子,是多好的事情!”
跳绳队员中极少有人关注其他体育项目。偶尔一两个表示对体育“很了解”的学生表示,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员是篮球运动员姚明和游泳运动员孙杨,偶尔会看中国女排的比赛,但没记过运动员名字。与体育巨星身上的商业代言相比,他们得到的赞助也微乎其微。
拨款和筹来的钱往往仅够支付必需的路费、食宿费和报名费。队员们几乎不会到赛场和住处以外的地方玩耍。在挪威比赛期间,他们的消遣是回住处途中,去海滩上转了转,在附近超市逛了逛。大部分人都没买什么,因为只有极个别孩子会带钱。他们的行李箱一半被运动鞋和跳绳所占据,每个人都背了十几根比赛用绳和备用绳漂洋过海。
即将升入初三的队员张敬威是“极个别”孩子,他用800元人民币兑换了约1000挪威克朗。17个孩子唯一的挪威购物经历就是在住处旁的超市,张敬威请队友在超市里吃了6份冰激凌,折合人民币近160元。他此前拿到了2块金牌、1块银牌和1块铜牌。
对此,他的感受是:“太贵了,回来能请全跳绳队同学吃冰激凌。”
3
父母们对跳绳冠军从来没有奖金略有微辞,但他们最大的顾虑还是担心影响孩子的学业成绩。对于跳绳,一般的态度是“既不支持,也不特别反对”。
从七星小学毕业后,岑小林和同年级的队友升入花东中学。为了承接这批世界冠军,花东中学在2016年组建了跳绳队,由体育教师带领训练,并从校外聘请教练进行每周两次的指导。为了准备挪威世界杯赛,他们在距比赛一个月时集训,这让他们错过了期末考试和大半个暑假。
2019年,花都区两所国家级示范性高中首次把跳绳项目纳入体育特长生招生项目。这成为父母同意他们留在跳绳队的主要原因。
“把跳绳的精神用到学习上,然后更好地学习,就是跳绳的目的。”一名10岁的队员半开玩笑地解释跳绳和学业的关系——这是教练告诉他们的。
有人认为,跳绳队采用的“半蹲式”跳法——长时间弓着背、正抬腿,影响了孩子长个子,放眼望去,跳绳队员的确比同龄人普遍要矮。赖宣治认为这与遗传有很大关系。
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技术总监胡平生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解释,对于青少年来说,跳绳能够促进长骨两端的骺软骨增生,进而促进长高。跳绳对膝盖的冲击比慢跑要小,同时能够强化心肺功能与肌肉耐力,增强眼、手、脚的本体觉,提高敏捷性与协调性。他建议,根据不同身体素质、跳绳技巧掌握程度,进行适量运动。
也有人认为加入跳绳队很残酷,让孩子们失去了快乐童年。
“什么叫快乐童年?”赖宣治反问,“如果他们自己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那还有什么快乐可言?难道他不在这里跳绳,就会有快乐童年吗?”
上中学时,赖宣治曾是篮球特长生,并凭此身份考进大学。他认为“体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让他找到自信,学会坚持。他也相信,体育能改变自己的学生,“孩子变化是能看到的”。
2014年,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首次举办全国跳绳联赛。七星小学跳绳队参赛,坐在观众席的校长张有连看得哭笑不得:第一次参加大赛,有孩子因为换了起跳的位置而不知道怎么钻进绳圈。尽管如此,这支队伍在80%的比赛项目中获得了奖牌,并拿到团体冠军。
接下来的一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八届亚洲跳绳锦标赛上,七星小学学生获得金牌34枚、银牌8枚、铜牌8枚,并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首届世界学生跳绳锦标赛上,他们拿下了28块金牌中的27块。2016年,在瑞典举行的世界跳绳锦标赛中,这支队伍成为中国在世锦赛上的首个团体冠军,并且出现了“世界跳绳大师”称号获得者和世界纪录保持者。
此类荣誉使七星小学从一所薄弱的乡村小学变成了明星学校,成为花都区教育局在推进阳光体育运动过程中“精心培育出来”的代表。
花都区教育局体育教研室副主任姚灿华介绍,区教育局在经费上全力支持,七星小学关于跳绳的经费申请基本都是全额拨付。区里还会组织其他学校的教师去七星小学观摩。当地举办的大型活动,也会安排跳绳队的表演。
七星小学教导主任江永滔认为,这些经历让学生们“更独立,视野更宽阔,性格也更好”。
看到外国运动员的花样跳绳,队员们觉得“开眼”,在场地里跟着欢呼。好些动作是他们没见过的,“很高级”。他们也会暗暗在场边学习,尽管“有的动作能学会,但第二天就忘记了”。队员张崇杨夺下世界杯花样跳绳个人冠军,他的很多动作是在国际大赛上学会的。
即将升入五年级的谭瑶是全国冠军。她在两年前的体育课上被选中,就是否参加跳绳队,回家征求意见。“如果你进跳绳队,就要坚持下去,不能说不练就不练了。”这是妈妈的回应。让她妈妈欣慰的是,自进入跳绳队那天起,女儿每天5点半起床去学校训练,从不赖床,从不喊累。
但孔荧莹认为,要总结跳绳迄今给自己“带来哪些变化”,是“比拿冠军还难的事”。
赖宣治几乎逢人必讲的一个场景是,2014年首次参加的全国比赛上,11岁的队员张茂雪把自己的全部金牌摘下来,挂到他的脖子上。“老师,我很开心!”这是她进队一年多主动对老师说的第一句话。
看到10岁的队员因为失误在场边痛哭,他觉得,这正是跳绳队的“底蕴”所在,“他想赢,内心对胜利有渴望。”
4
全队都知道,岑小林背负的任务“不是拿金牌,而是要破纪录”。
训练时,队员们互相帮忙计数。9岁的廖娅琦最怕的不是比赛失误,而是给岑小林计数,“跳太快了,看不清,尤其他的脚,一上一下的。”
在国外参赛,这些只学过简单英语的中国孩子,能听懂英语报出的参赛号码和姓名。队友比赛时,他们用教练的手机帮忙录下视频,以备裁判错数或漏数时,用作申诉的证据。
在速度跳绳领域,国内赛远比国际赛竞争更激烈,因为不是所有的国内跳绳高手都会去参加国际比赛。中国跳绳国家队并非常设机构,而是为备战世界大赛而组建。据陈阳辉介绍,一般来说,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是从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全国跳绳锦标赛、中国国际跳绳公开赛这三大赛事中,挑选单项排名位列前三的运动员,再筛选组建国家队。
七星小学在国内的对手也拥有很多世界冠军头衔。比如,在美国举行的2018年跳绳世界杯赛上,广州的东荟小学跳绳队拿到了23个冠军,济南的辅仁学校则收获了48枚奖牌。
跳绳队的比赛场地通常有1.5个篮球场那么大。几组比赛可能同时进行。广播里在计时提醒,运动员脚掌砸向地面发出“哒哒”声,还有看台上观众在尖叫——每当大屏幕上实时更新的数字开始向世界纪录靠拢,赛场上声浪迭起。
在挪威比赛时,岑小林能清晰地听到教练赖宣治的声音——他会蹲在比赛场地旁,发出队员们熟悉的“赖氏狮吼功”,从小声计数直至喊到声嘶力竭。岑小林起初根据提示“保持节奏,不要加(速)”,在最后30秒,他全力加速,跳到脚掌发烫。
最后,他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将男子3分钟单摇跳绳的世界纪录由1136次改写为1141次。半个月后,他在全国跳绳总决赛上又将这个纪录提高到1152次。
每年的世界性跳绳大赛分别由国际跳绳联合会(FISAC-IRSF)和世界跳绳联合会(WJRF)举办,现今两个组织合并为国际跳绳联盟(IJRU),挪威比赛是世界跳绳联合会最后一次单独举办的世界杯赛。闭幕式上,打破5项赛会纪录和1项世界纪录的岑小林受邀在国际跳绳联盟首面赛旗上签字。他小学二年级进入跳绳队,四年级拿到全国冠军,五年级开始破世界纪录。
由贵州老家到广州读书前,岑小林曾随父母、姐姐和哥哥在北京打工一年。“爸妈说我还小,一直打工也不是办法,想在北京那边读书的。”岑小林回忆,姐弟3人在北京的学校面试,校方要求年龄差别很大的3个孩子都必须要从一年级读起。岑小林的父母拒绝了。
后来,经人介绍,一家五口再次迁徙,坐上了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大巴。父母在菜市场卖菜,三个孩子进入七星小学,分别入了一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
随着像他这样的孩子带回越来越多的奖牌,“绳文化”被七星小学写进了办学理念、办学目标,这所建校50多年的学校也有了自己的校训:“悦动至善 和乐致远。”
校门口的6块展板上,4块用于展示那些与跳绳有关的荣誉。新教学楼阳台上写着“绳以育德”四个大字,强调“从这里走向世界”。在这栋楼一楼最显眼的位置,是岑小林、韦杏亲、张崇杨等跳绳队员的照片。
有些人已经在一次次迁徙中告别了这个以他们为荣的地方。韦杏亲在2016年瑞典获封为“世界跳绳大师”,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因为家庭原因,她不得不在2018年9月放下了手中的跳绳,回到广西老家。
廖娅琦出生后不久被父母从湖南带到广州。她只有9岁,记得自己搬过9次家,而她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搬家。她当初是主动“在体育课上举手”加入跳绳队的,梦想是“当一名裁判员”。
整个跳绳队里,年龄最小的世界冠军是10岁的钟炜锋。在挪威世界杯赛上,他拿了7块金牌。全家人守着网络直播关注他的比赛。他的姐姐钟银燕说,家里人很紧张,有一段时间关机不敢看。看到弟弟跳绳时的表情,他们感到心疼。“我奶奶和我妈妈看着看着就哭了。”钟银燕也曾是跳绳队队员,今年考取了跳绳中级裁判证。今年,她考入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等待入学的日子,回到小学义务做教练。她的弟弟妹妹都在跳绳队。
一家几个孩子在跳绳队的现象并不少见。去挪威比赛的17人名单上,张茂雪、张崇杨、张崇霞是亲姐弟;更早的名单里,岑小琼、岑小会、岑小林、岑泽忠是表亲,都是世界冠军。岑泽忠如今进了一家跳绳俱乐部做教练,岑小林本该和姐姐岑小会一起回贵州上学,但是老师多次家访,把他“拦截”下了。
岑小林很清楚,如果回到贵州,他就可能成为留守儿童,父母就可以换一个地方打工。为了支持他的跳绳生涯,他们已经在这里守了他7年多。在赖宣治看来,跳绳能够改变学生的命运,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这条绳子把他们留在了这里,不用跟他父母四处漂泊、辍学打工,能读书就有机会。”
父母其实不怎么关心岑小林的比赛,更在乎他的学业,希望他能安安静静读完书,找一份好的工作。他们对“好的工作”没有定义,岑小林的理解是:“应该就是不要像他们那样辛苦,也不用回去种地。”
岑小林的理想是当一名体育教师,“将来教人跳绳”。长远来看,这或许是个前景不错的选择——很多地区已经将跳绳纳入了中考体育考核项目和小学生体质测试的必测项目。“这意味着,我国上亿学生中的绝大部分都会在学校中接触到跳绳运动。”陈阳辉说。近10年来,国内出现了专业的跳绳俱乐部和跳绳器材、培训、演出方面的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约有50家跳绳协会和100多家专业跳绳俱乐部。
现在,跳绳界的巨星岑小林只是受到体育老师钟爱的一名中学生,和同批“起跳”的队员继续着第七年的跳绳训练,为更多的世界纪录,也为了“将来教人跳绳”。
在不需要跳绳的日子,他们会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清晨跟父母到大棚,一直劳作到傍晚。同样在花棚工作,这里有不少湖南人种植绿萝,同时有不少贵州人负责插花——把绿萝的秧苗剪断,然后栽到花盆里。因此,湖南孩子擅长给绿箩剪苗,知道“110”和“180”型号花盆的区别;贵州孩子会坐在闷热的大棚里插花,“坐到屁股痛”。很少有孩子不会做饭,他们通常负责自己和家人的晚饭。在大棚里,他们偶尔会遇见队友,那很可能是另一个世界冠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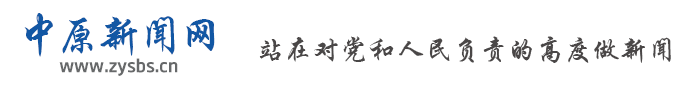
 0310-3111082
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30477986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