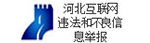一个向“人民楷模”朱彦夫同志学习的热潮,正在齐鲁大地兴起。
许多人在学习中思考:这位四肢全无、失去左眼、头部背部还残留着弹片、腹部有严重刀伤的特残军人,在其重伤致残后的漫长岁月中,忍受着比常人多得多的痛苦,经受着比常人多得多的磨难,艰苦跋涉,不懈追求,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的人生足迹,是什么支撑着朱彦夫走过了艰难却又辉煌的历程?
《大众日报》日前刊发三篇通讯,并配发三篇评论,为读者揭示朱彦夫身上的三个特质。
忠诚
忠诚为党一心为民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10月11日,一场雨后,天气渐凉,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的山路薄雾环绕,漫山的青色有些泛黄,路边的野花在风中摇曳。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拼来的,我们要时刻深怀感恩之心。”已是耄耋之年的朱彦夫虽然饱经风霜,但话语之中、眉眼之间,依然流露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
在朱彦夫家里有一样东西,他视若珍宝,那是他在战场上荣获的3枚军功章。在他看来,军功章不仅包含着对军旅生涯的回忆,更是党和人民给予的最高奖赏,它像一面镜子,照射出革命战士对党忠诚的深度和纯度。
童年苦难的岁月,家仇国恨,在他的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抗争的种子。1947年,年仅14岁的朱彦夫参军入伍,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等战役战斗上百次,至今他的头部、背部还残留有弹片。解放上海时,16岁的朱彦夫只身炸毁敌人3座碉堡,身负重伤,荣立战功,火线入党。
“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准备一次性把自己献出去。”朱彦夫曾在作品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1950年冬,抗美援朝战场,朱彦夫所在部队经过浴血奋战,成功拿下了二五〇高地。来不及休整,他们就接到命令:死守高地。
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中,炮弹像雨点般砸在高地上,朱彦夫和战友们舍生忘死,在没有后勤补给和弹药补充的情况下,硬是打退敌人十多次进攻,但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到第三天,仅剩的朱彦夫也被手榴弹炸昏,重伤倒在阵地上。
昏迷中,朱彦夫觉得还在与敌人战斗。他越打越渴,越打越饿,一块黏糊糊的血肉顺着鼻梁滑到嘴边,他本能地一口吞了下去。彼时的朱彦夫哪里知道,他吞下去的竟是自己的眼球。
失去四肢和左眼的朱彦夫想到死,但连死的能力都没有了。冷静后的朱彦夫很快重新燃起了斗志。“身体虽然残废了,但我的心还是完整的,我要用一颗火热的心报答党和人民。”朱彦夫说,为了死去的战友,也必须活下去。
“当干部,就是要把心掏给百姓,以心换心,群众才会信你、认你。”1957年,回到家乡带领群众建设家园的朱彦夫,开始了另一场“战斗”。当时,张家泉村原来的党支部班子涣散,两年内换了3任书记,也没能带领群众走出困境。朱彦夫上任后,通过抓班子、强建设,村风、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1973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路冲毁车不通。从博山采购架电材料回来的朱彦夫,掏了掏身上所剩无几的钱,只好雇了头毛驴返回沂源。由于山路高低不平,朱彦夫两只残臂抓不住缰绳,好几次从驴背上摔下来,倔强的他又一次次爬上去。当走到博山与沂源交界的松仙岭时,赶驴人实在不愿意送了,朱彦夫只好拄起双拐,一步步往前挪。赶驴人不忍心,又追上来问明底细。当他得知这个没有手和脚的人是在为村里架电奔波时,马上把毛驴拽到朱彦夫身边,将他送回村里。
7年间,朱彦夫跑油田、去上海、闯西安、下南京……先后79次外出,行程7万多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备齐了价值20多万元的架电材料。1978年12月,全长10多公里的高压线路跨过一道道山梁、一道道沟壑,终于接到了村里。
时至今天,朱彦夫都清楚记得,通电那天,张家泉村村民都守在电灯下,眼瞅着,守了整整一夜。
担任村支书25年间,朱彦夫忙忙碌碌为村里办事,他的家曾是村里的识字班课堂、免费医疗所、村委办公室;他没吃过群众一顿饭,上级每月分配给他的白面、红糖,他也总要分一些给四邻八舍的老年人和五保户。
朱彦夫有抚恤金,是全县唯一吃“国库粮”的村支书,可他家里也会时常连盐都没钱买。因为他把微薄的抚恤金用作村里的发展基金、慈善基金。这些钱,当年是乡亲们公认的救命钱。
在日常生活中,妻子陈希永总是想方设法从自己嘴里省下粮食,留给老人、丈夫和孩子,每年青黄不接时,她经常要靠吃野菜、啃玉米芯、吃槐树叶子等充饥,因为长期吃,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
靠着“打铁先得自身硬”的坚定信念,张家泉村支部班子真正锤炼成了一个团结奉献、为民务实、敢打硬拼的战斗堡垒。
“老书记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也是一任接着一任干,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心头。”张家泉村村委会主任刘文合说。
眼下的张家泉村,玉米堆满了墙根,苹果挂满了枝头,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村民的脸上!朱彦夫心里始终装着村里的父老乡亲,村里的父老乡亲也始终挂念着他。
执着
执着奋斗,永葆初心
入秋之后天气渐凉,最近的几场秋雨更是让朱彦夫的旧伤隐隐作痛。这位86岁的老英雄半躺在床上,但他眼神中依然透着坚毅和力量。
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朱彦夫,先后作了47次手术,两腿从膝盖以下截去,两手从手腕以上锯掉,失去了左眼,右眼的视力仅剩0.3。
“说句大实话,如果我不是党员,忘记了举拳头,器官早就萎缩了,精神早就崩溃了。我老朱心里要不是装着党,装着共产主义,早就死了。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啥?先做个能自理的人吧。”朱彦夫说。
他最先双臂碴夹起勺子,还没等靠近碗沿,勺子就掉了;用嘴叼起勺子再用臂碴夹紧,方向把握不准,又把碗碰翻;重来……一个动作每天要琢磨练习成千上万次,一气练了几十天。在别人看来,这份执着甚至有些倔。
终于自己能吃了,他兴奋不已。又对准了下一个目标——站起来!
他先让人帮着装假肢,后来,又偷偷自己装,但是每次都摔得血肉模糊。反反复复练习之后,终于靠自己一人装上了,朱彦夫兴奋得一下子从床沿站起来,感觉自己高了许多,可还没站稳又摔倒在地。
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四肢的创伤面刚结痂,又被磨破,鲜血直流,浸透了衣服和腿套。
朱彦夫又一次顽强地站了起来。他挑了病房外一棵最高的杨树,并排站着,但没靠着。终于,他看一切,不再是仰视。
从1996年患脑梗塞至今,朱彦夫半身不遂,右侧身体失去了知觉,甚至连穿假肢行走的“权利”都没有了。清醒后他交待儿子,在自家的天花板上,安了一只带铁链的吊环,他用那只还能活动的左臂,每天牵引锻炼上百次。除此之外,他还坚持每天甩臂扩胸两个小时以上。他不能失去行动的能力,不能降低自己的“幸福指数”。
“你一定要记住,一个连的消亡,在战争史上可能不算什么,可你要想法儿把这壮举记录下来,告诉后人,我们死也瞑目了!”朱彦夫至今仍记得连指导员高新坡弥留之际的嘱托。
“我不会写,就用口说吧。”
从1952年开始,到1996年突发脑梗塞倒在讲台上,44年间,朱彦夫拖着残腿,每请必到,奔走大江南北,无偿作了1000余场报告,听众达几百万人。为了作报告时不上厕所,他不敢喝水,每一次都讲得口干舌燥。
每作一场报告,朱彦夫就像大病一场。但为了战友的嘱托,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曾经的苦难与辉煌,珍惜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与美好,朱彦夫觉得,值!
作报告仍有局限,朱彦夫又作出一个决定——写书。
为了写书,朱彦夫翻烂了四本字典。他用残臂翻页,有时干脆把脸贴在字典上,用舌头一页一页地舔……刚开始,他用嘴含笔写字,每天只能写十几个或几十个字,口水连着汗水,泪水和着墨水,弄得字迹模糊。后来,他残臂夹笔,每天能写上百个字,甚至五六百字。儿女们劝他口述,但他坚持自己写,他已把写作当成磨砺意志的方式。
整整7年,一天学没上过的朱彦夫,用掉半吨稿纸,先后七易其稿,终于写成了33万字的长篇小说《极限人生》。
拿到新书的当天,朱彦夫把自己关在屋里,打开书的扉页,恭恭敬敬写满了牺牲战友的名字,然后,颤抖着划着火柴,将书点燃。朱彦夫哽咽着说:“指导员,书出来了,你的遗愿实现了,你看看吧……”
张家泉村纵贯着三条深沟,最宽的地方有100多米,把全村分割得没有一块像样的土地。回乡担任村支书后,朱彦夫提出,用锄头和独轮车,向荒山和沟壑要耕地,全村吹响了向贫困宣战的号角。
整整几个冬天,朱彦夫像一名不知疲倦的战士,拖着17斤重的铁腿,和全村上百号劳力一起住荒山,填深沟,造梯田。
现任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刘文合告诉记者,当时的工程量非常大,石头都是从千米外的山上用小木车子推下来的,然后从别的地方取土填起来。光这样就增加了70多亩良田。
有了地,缺水问题又突显出来。张家泉村原名张家庄,是个有名的缺水村,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吃水都是难题。
1971年2月,大雪纷飞,滴水成冰。朱彦夫带领全村380多名劳力,分成7个施工组,昼夜不停地修建大口井。
数九寒天里,朱彦夫拖着假肢不停地在水利建设的工地上走动着。挖到10多米时,朱彦夫不放心,坚持下到井底去看看。等到大伙把他拉上来时,朱彦夫觉得残腿疼得很厉害,假肢怎么也卸不下来,原来是井里的泥水、腿上的汗水、断肢创面渗出的血水,已把假肢和残腿冻在一起。
经过一个冬天的苦战,龙王庙大口井终于竣工了。张家泉村有了历史上第一眼大口井!张家庄正式改名为张家泉。
为了引水上山,朱彦夫六上省城,十进县城,请水利专家帮助测量和规划选址,购买引水设备,修建了1500米长的高架水渠,使全村300多亩旱地成为水浇田。如今,张家泉村凡有果树的地方都能浇上水,家家户户吃上了自来水。
大口井里的水已经流淌了半个多世纪,让村民吃上了饱饭,鼓起了腰包,更滋润了百姓的心田。
朴实
朴实做人,无私奉献
10月,淄博市沂源县张家泉村,漫山果树枝头上热闹起来,挂满一个个“沂源红”苹果。看到当年的荒山生机勃勃,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曾经的村党支部书记朱彦夫满怀欣慰。在朱彦夫家,86岁的老英雄坐在床上,依旧是战士的英姿。
1947年沂源解放,那年冬天,14岁的朱彦夫穿上了军装。让他自豪的是,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等上百次战斗中,他都立过战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朱彦夫失去四肢和左眼。是一辈子在疗养院被人伺候,还是回老家?“去”还是“留”,如当年的“生”还是“死”一样,摆在了他面前。最后,他作出决定:不能让国家养起来,我要回家。
1956年春,主动放弃荣军休养所特护待遇,朱彦夫毅然回到家乡——沂源县张家泉村。1957年,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人生的第二个“战场”,与乡亲们一起奋斗25年。
一上任,朱彦夫就拄着拐,拖着17斤重的假肢,臂上搭着块随时擦汗的毛巾,深一脚浅一脚,到田间地头查看生产,逐门逐户查访民情。主意慢慢拿定:治山、治水、造田、架电。一个个山里人想都没想过的大工程,在张家泉村热火朝天地展开。他始终掌握第一手资料,春天的耕播、用肥、苗情他了解;夏天庄稼长势、旱、涝、虫、草荒他知道;秋天庄稼收割、打场情况他说得清;冬天整地、积肥状况他了然于胸。
全县第一个有拖拉机、第一个平均亩产过600斤;全乡第一个用上电、村民人均收入第一……谁能想到,这么多“第一”,竟是张家泉村,这个建国初期村民连地瓜干都吃不饱、一到灾年就靠讨饭糊口的穷山村创造的。
在休养所颐养天年,不是很好吗?即使回到村里,也可以吃国库粮,衣食无忧,为什么非要干村支书这个苦差事呢?朱彦夫说:“虽然我没手没脚,但有心有脑,哪能吃闲饭?看到乡亲们连饭都吃不饱,我哪能袖手旁观?带领大伙过好日子,困难肯定不少,但再难,比战场上拼刺刀还难吗?与其腐烂,不如燃烧!”
那时候,村里没有办公室,朱彦夫家狭窄的屋子就是会议室。支部开会,一开就到深夜。他不止一次对全家人说:“咱家有特等残废这一个‘特’字就够了,绝不容许再有一个‘特’字出现!”
对家人严苛得近乎“残忍”,但朱彦夫对村民却百般呵护。他的大女儿朱向华告诉记者,父亲每月的伤残金,大部分都用在了集体的事和接济村里的穷人、病人上。上级每月配给他的白面、红糖,他也总要分一些给四邻八舍的老年人、五保户、病人和烈军属。家里的鸡蛋也不让孩子们吃,用作公务招待。公社、县城来人,到了吃饭点儿,他就自掏腰包在家里招待。。
前不久,张家泉村现任支书刘文合又来到朱彦夫家。一落座,朱彦夫就扒拉开自己的日记本,搓出一张纸条交给刘文合。这是老书记的习惯,自从朱彦夫患脑梗塞后,思维就难以一直清晰。看电视时,有什么致富项目和信息,觉得村里能用上,或者自己有什么建议,他就写下来,等村里来人交给他们。
朱彦夫是个发光源,释放正能量。在他身上,没有暮气,没有怨气,没有骄气,而是处处彰显着勤俭朴实的优良作风、感天动地的浩然正气。从1952年开始,到1996年突发脑梗塞倒在讲台上,44年间,朱彦夫拖着残腿,每请必到,奔走大江南北,无偿作了1000余场报告,听众达几百万人,所到之处,都会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
谈吐间,他有军人的豪气,也有沂蒙汉子的朴实。他常拿自己开玩笑,身上的伤疤每到阴天下雨就疼,他说自己是“天气预报”;假腿走在泥水里,他说这就是优越性,零上100度不觉得烫,零下100度不冻得慌。“我当了一辈子‘小偷’,14岁偷着去参军,从疗养院里偷着回家,当村支书也是瞒着家人偷着干上的。晚上想出门查看工程,老伴、子女都不让,我就偷着去。见熟人就躲到庄稼地里,要不让他们发现了就背着你、推着你,你就看不到想看的东西了,就不自由了。”在朱彦夫心里,“偷”是一种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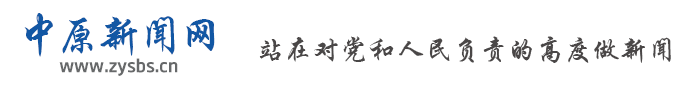
 0310-3111082
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30477986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