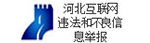白血病患者路炎衡,直到来北京的前一天都想放弃治疗。而路子宽态度坚决,“我能救爸爸!我家不能没有我爸!”
9月9日9时许,河南新乡辉县10岁男孩路子宽走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清河分院的手术室。采完500毫升骨髓,他坐在轮椅上,自己拿着输血袋,从手术室笑着出来。推着轮椅的医护人员说:“他真的超乎我们想象,这么懂事的孩子太少见了。”
孩童供者,总让医护人员犯怵。有13岁的女孩走到门口就是不进手术室,也有孩子在手术室里蹦来蹦去,还有人看到针就晕。
是的,为父亲捐骨髓的子宽并非特例。可他又的确是个特例。
进手术室前,母亲让子宽疼了想哭就哭。“我不哭!”他说,“我是个英雄,爸爸是美人。”

9月9日早上,捐完骨髓出来的子宽受到医护人员的表扬,姑姑赶紧接过他手里的血袋。 刘雪妍 摄
第一天
“动员”
9月6日早上7点多,子宽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清河分院打第一针动员剂。
由黄晓军教授领衔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是全球最大的单倍体移植中心。所谓单倍型移植,是指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堂表亲之间的移植,只要求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部分相合。这一技术方案被国内外同行称为“北京方案”,曾经两度登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领奖台。
按传统理论,造血干细胞移植(俗称骨髓移植)需要供者和接受者的人类白细胞抗原一致。因此,供体来源不足成为世界性难题。
子宽和父亲的配型,恰恰是半相合。
如果没有8年前那些变故,这个河南辉县百泉镇西井峪村的普通农家,会过着他们现在最期待的平淡生活。
2011年初,路炎衡家的龙凤胎出生,一大家子还沉浸在喜悦中,5月,路炎衡的哥哥和妹夫在跑运输途中被疲劳驾驶的货车追尾,双双遇难。当年26岁的路炎衡成了顶梁柱,跑前跑后料理后事。11月,他发现面色发黄、心慌、流鼻血,想着是劳碌过度,没放在心上。
不适感愈发强烈,路炎衡先后去了辉县市人民医院、新乡医学院一附院,被诊断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即白血病前期。
辗转到了北京301医院,医生建议他进行骨髓移植,可家里没这财力,也找不到合适配型。路炎衡选择保守治疗,靠服药维持了7年,农忙时还能开三轮车运粮。
去年8月,病情突然恶化,不输血就有生命危险。路炎衡的手上不见一丝血色,心脏承受重压,唯一的出路依然是骨髓移植。
今年3月,配型结果出来,10岁的儿子路子宽是最合适人选。
这个结果让全家人都无法接受,围坐着,只能哭。路炎衡坚决不同意,不断地说要放弃治疗,“孩子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能拖累他!”
医生反复告知,捐献骨髓对子宽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孩子恢复得也快。最终,路炎衡点头了。
子宽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比大人们坚决。听到自己只要胖到90斤就能作为供者,他拍了小胸脯,“我一定会让自己胖起来的!”
当时体重只有60斤的子宽,身材与名字相反,精瘦得像个小猴。
增肥,成了他生活的主题。3个半月,他从60斤增至97斤。
终于可以打动员剂了。这是一种名为“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的药物,用在捐赠者身上是为了动员造血干细胞至外周血,使其数量足够移植所用,捐髓前会按体质差异注射4到6天。
有病友家属告诉子宽这针不疼,他嘟囔:“针没打在你身上,你怎么知道不疼?”
大人之间聊起治疗,没人留意到孩子小声说了什么。他胳膊上的针眼,每天都在增加。护士夸他勇敢,他就打趣姑姑按压止血时比打针还疼。
“我的细胞现在开始往外跑了。”他冲着护士笑,也对记者笑,眼睛又笑没了。这些细胞,将成为父亲生命的“动员剂”。

子宽和弟弟妹妹的合影,是路炎衡所有社交平台账号的头像。增肥前的子宽(左一)只有60斤。
第二天
“礼物”
路炎衡身份证上的数字是其农历生日——这是9月7日子宽的姑姑与记者交流时说的。记者一看日历,今年生日不正是9月9日采骨髓的日子?
一家人忙乱得早已忽略路炎衡的生日。探视时,记者隔着玻璃打电话与路炎衡提及这事,路炎衡哭了。无菌舱内的他,发布了一条朋友圈:“儿子给了我一个珍贵无比的生日礼物……感谢儿子为我付出的一切。相信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生日和重获新生,安排在了一天。”
子宽得知后,睁大眼睛,拉住母亲李金鸽,歪头说:“我送给我爸的生日礼物是骨髓。”他眯眼笑了,“其实是一条命啊!”子宽重复了两遍,母亲眼眶又红了,孩子其实什么都懂。
很多人最初认识这个10岁男孩,是从河南新乡电视台的新闻里——大盆的红烧肉,煎煮炒的鸡蛋,他胖胖的手抱着大碗,大口吞咽,明明已经饱了,含着泪还要再多塞几块肉,多喝几口奶。
每天早上称重,数字的增长是子宽塞下每口饭的动力。每增重一斤一两,他都骄傲地向父亲报告。
每天三餐都吃到胃发胀,但他临睡前还再逼自己吃碗泡面。吃得太难受时,他放下筷子发愣,嘴边挂着面条,3个煎蛋还等在盆中……“每天都数不出来几顿,只要感觉能吃下他就吃。”母亲看着儿子吞咽得难过,既不忍又无措。
家里的餐桌从没有这么密集地出现过荤菜,都是在超市上班的母亲带回的打折肉。弟弟妹妹虽然也想吃,但懂事地把荤菜留给哥哥,而子宽会趁爷爷奶奶不注意,给他们碗里放个鸡腿。
路炎衡的微博,忠实记录了儿子变胖的过程——体重增长到穿不下衣服,再到走路时大腿根的肉被磨烂。
原本心脏就疼的父亲,看着无比心疼。
再看到子宽的体检报告中有轻度脂肪肝时,路炎衡更为难受,“短期增肥对孩子身体有伤害,我特别亏欠他,没有给孩子们创造一点物质条件,还让他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他甚至觉得自己“给孩子的童年添加阴影了”。
子宽则在慢慢适应自己变得很有负担的身体:走路时,他习惯性把双腿分开,灼烧感没有那么强烈了;以前他喜欢跑步,现在只跑几步,头上的汗就像被雨淋过一样,那就索性少跑。
“爸爸你放心,我现在是家里的小男子汉,等你病好了再来当大男子汉吧。”刚放暑假,子宽就接过了母亲的棒,推父亲去医院输血,上医院门口大坡时,小小的身体用足力,直喘粗气。

路炎衡听到记者说,生日那天孩子要送他特殊的生日礼物时,哭了。 刘雪妍 摄
第三天
“大山”
9月8日,捐髓前一天,要化验血常规。短期增肥的子宽,胳膊上的血管难找,白挨了一针,姑姑有点难受。他安慰姑姑说没事,奶奶包的饺子快送来了,是他最爱的猪肉芹菜馅。
医生给家属们开会说,每个病人身后都有三四个后盾,这是在一起打仗,要配合好。
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战争,甚至需要举家族之力。
更何况,对于这个典型的中国农村家庭而言,治疗费是如影随行的大山。
家里种了两亩多小麦和小米,一年收入三四千元;李金鸽在超市打工,月入2000多元。路炎衡生病这几年,住院吃药已让家里举债,骨髓移植至少需要50万元——这数字根本无法想象。
“我体重够了,但还不手术,肯定是没钱了。”6月最后一天,子宽已有96.7斤,可手术还是没影的事。家里准备卖房,可这农屋许久也无人问津。
一向要强的爷爷,丧子时没流的泪,这次流了:既记挂儿子,也担心孙子。奶奶更是整日肿着眼。
他们去找亲朋借救命钱。一考虑偿还能力,有的亲戚拿几百元出来,说还不了就算了,甚至有亲戚说他们借钱没诚意。
听说蝉蜕能换钱,一放暑假,子宽就带着弟弟妹妹每天去村边杨树上捡蝉蜕。尽管,3个孩子每天拎回来的一袋只能卖2元钱。
夜里,子宽还会跟爷爷奶奶去捉蝎子,在人烟稀少的地里或岸边,用紫色的灯照,拿镊子夹起变荧光的蝎子,捉进罐子里。子宽毫不害怕,因为,3个晚上捉的蝎子能卖100多元。
可这些对手术费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直到路炎衡给当地电视台打出电话,媒体涌入子宽家,困境才得以摆脱。
黑洞洞的摄像头对着,上面还架着话筒,屋里只留子宽一人,没人教他说什么,他就自己开始了:“我叫路子宽,是个胖胖的人……”
他的笑脸招人喜欢。视频下方,网友评论:“路子宽小朋友,你以后的路子一定会宽的!”
仅仅半个月,捐款达到近百万元,手术费终于有了着落。
一家人赴京看病的前一晚,从辉县输完血,路炎衡说要自己转转。正在收拾行李的李金鸽,忽然收到路炎衡微信,让她退掉去北京的高铁票。“我们当时特别着急,给他打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只能坐在家里等。”
临近半夜,路炎衡骑着电动车回了家。沉默许久,他还是让妻子继续收拾东西去北京。
李金鸽后来才知,丈夫那天晚上是怕了,真的筹够了钱,心里却没底,“因为这一次就到生死之间,成为弦上的箭了”。
第四天
“敌人”
9月9日,子宽在等候采骨髓的半个多小时里,只是安静坐着,术中还陪着医生聊天。医生告诉他已经结束时,他说:“这么快!我还没觉得疼呢。”
实际上,采骨髓前一夜,子宽醒了五六次,不停问陪床的姑姑天亮了没。清晨5点多抽过血,他就睁眼等着进手术室。
这个漫长的夜晚,路炎衡也没睡好。之前妻子探视时,他因为疼痛和害怕,流泪了。李金鸽告诉丈夫不能哭,“要战胜病魔,你弱它就强”。
进无菌舱前,路炎衡还笑着对妻子说,“每天我要吃炖排骨、牛肉、羊肉”,而化疗真的开始,他难受得一口都吃不下。
“每天送新的饭,拿老的回来,经常都是原封不动。”李金鸽说,只要医生不说禁食,家属都会坚持送,哪怕病人吃完吐出来也好。
每天3顿饭,她从早上5点多开始准备,水果也要蒸熟,一个橙子9.3元,她原来从没买过这么贵的,路炎衡却没吃一口。
给丈夫做饭要无菌化,李金鸽恪守这一点——荤菜只敢买活鱼活虾,西兰花等不易清洗的蔬菜不能买,做菜要少油少调料;饭盒洗干净后放进消毒柜,用之前在开水里再煮30分钟;送进无菌舱的所有东西,医院都会再进行一次高温灭菌,所以不管是餐具还是吸管都要套双层塑料袋,中间加一点清水隔热防止变形。
李金鸽到现在也想不通,“好好一个人,怎么就不造血了呢?”子宽奶奶也一直在问,“你说怎么就得了这种怪病?”
为什么是我?这事为什么发生在我家?得病的人和家属问了无数遍。
即使在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例在亚洲领先的医院,也没有医生能给出确切原因。
有朋友打电话来问康复时长,李金鸽难以回答,骨髓移植结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之后他就和一个婴儿一样,更要好好保护”。
“万里长征第一步”,这话在病房走廊里听得最多。
病人们被照顾得细致,家属们对自己就没那么讲究了:前一天剩下的包子,放了一宿的面,就一点咸菜,就是今天的早餐。
三十出头的女人,正吃着饭就放下筷子,带着哭腔说,“在医院怎么这么难熬?比干什么都难熬!”
觉得难熬的时候,子宽会打一会儿游戏,虽然“平时上学的时候根本就想不起来玩”,而今却可以让他放松。他一枪枪打倒“敌人”,大喊大叫,就像自己的健康细胞向爸爸体内的坏细胞发起攻击一样。
游戏里的人拥有酷炫武器,还可以无限次复活,但问他是否想活在游戏里时,他果断回答:不想,因为“家人都不在”。

9月6日下午,子宽和妈妈、姑姑一起去探视爸爸,他让爸爸安心,好好吃饭,自己也会加强营养的。 刘雪妍 摄
第五天
家人
9月10日的采血从早上8点半开始,干细胞采集室里的供者陆陆续续出来。5个小时过去了,路子宽的名字还没被叫到,母亲和姑姑等得有些着急。终于见到他时,孩子眼睛肿肿的,说自己头晕,他举起手数着,“我现在身上的针眼得有20个”。
原以为采完骨髓就能先出院,等第二天再来采集造血干细胞,没想到大腿内侧采髓后埋了针,要多住一晚。一听到不能出院,采骨髓都没哭的子宽一边输着血,一边噘嘴哭了。
母亲以为他是在医院住得太难受,鼓励他要懂事,坚持到最后一天。不料,子宽说:“不出院就不能去看我爸。”
虽然同在一栋楼里,住院的子宽却不能从11层上到15层去看父亲。他掰着指头数,“我都3天没去了”。
路炎衡可能不知道,子宽特别崇拜他——爸爸骑摩托车既快又稳,还会修很多东西。“这手机就是我爸修好的!”他拿着姑姑的手机给记者看,言语里满是骄傲。
住院前,医院附近的租房是路炎衡张罗的。楼层很高,子宽说:“高了空气好,卫生,这可是我爸找的!”在他心里,爸爸永远就是那个骑车载他吹风涉水,无所不能的爸爸。
来的记者越发多了,一次子宽对母亲说:“我不想让记者来了,问得我伤心。”因为,竟有不止一位记者让他假设,如果有天爸爸忽然离开了……
为父亲捐骨髓的子宽,在医院里并非特例。但懂事至极的他,又的确是个特例。
血液病区走廊的患者家属看到子宽,会直接说,“这供者体格真不错”,语气平常。记者采访数日,见到了不止一位孩童供者,有个9岁小姑娘也是为父亲捐骨髓。
还有一个13岁女孩,为母亲捐骨髓,快进手术室时突然反悔,任凭父亲和护士怎么劝都只不动弹;等父亲换上全套衣服陪她,她才磨蹭着进去;骨髓采完后她不肯下床坐轮椅,可没人抱得动体重140斤的她,医护人员只得启用备用床把她推出去。
截至今年8月31日,中华骨髓库的捐献造血干细胞例数为8800,患者申请查询人数为81799。
如果库容更大,如果患者找到合适配型的机会更多,像子宽这样的孩子或许就不用承受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眼下,子宽很想回老家,“想弟弟妹妹,想小伙伴,想去大队玩”。
正是山楂成熟的季节,家里几棵大山楂树,“结的山楂可大可漂亮了”,奶奶煮的山楂水,是子宽迅猛增肥时觉得最好吃的健胃药,也是路炎衡化疗难受时尤其想喝却不能喝的。
子宽巴望着,到明年山楂红遍树梢时,就能和爸爸一起喝奶奶煮的山楂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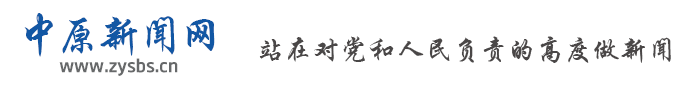
 0310-3111082
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30477986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