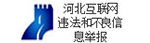2019年12月3日,李建功(左)与律师王誓华从法院走出来。受访者供图
走出法院的大门,51岁的李建功突然哭了起来。一旁的法警说,“出来了,应该高兴。”他用胳膊擦了擦泪,没有说话。
12年漫长的“马拉松”走到终点。昨天(12月3日)上午11点,曾获死缓的李建功,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
51岁的李建功变化很大。妹妹说,昨晚和家人吃饭时,他话不多,也没有笑脸。走路时,也常常低着头,没有精神,像60多岁的老头。
“12年的冤屈,终于真相大白,我哥哥自由了。”妹妹发了一条朋友圈,并配了四张合影。照片中,李建功表情木然,看不出喜悦还是难过。
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他提到,此前的生活轨迹,因为这一场无故的灾难,完全改变了。之后,他将会提起国家赔偿,并要求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入狱前的李建功。受访者供图
厕所陈尸
时间回到2007年12月3日11时,新疆库尔勒水泥厂,居民崔香海与王江海,在住宅区附近厕所掏粪时,发现粪坑内有一具尸体。
辖区刑警接警后,赶到现场,并把尸体从厕所粪池内打捞上来。经辨认,死者为水泥厂退休职工曹菊英(女,75岁),经农二师公安局法医现场尸体检验,死者头部有钝器击打伤痕,是被人用胶带封住口鼻,窒息而死。警方认定,这是一起熟人作案、就近杀人、就近抛尸的案件。
办案人员为了查找杀人工具和死者携带的物品,搜查了死者的家,并掏空了粪池内的粪便,但一无所获。随后,办案人员排查了与死者有关的人。
六天后,死者的邻居李建功,被锁定为嫌疑人。对此,李建功的辩护律师王誓华提到,法医鉴定,曹菊英死亡时间考虑在2007年12月1日下午。当警方排查到李建功时,没人能证明他当日的行程,而且,李建功在接受询问时,遗忘了他12月1日下午在家附近卸载葵花杆的事实。警方因此怀疑,李建功在卸葵花杆时,与曹菊英发生冲突,并把她杀害。2008年12月9日,李建功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3日被逮捕。
起诉书认为,2007年12月1日16时许,李建功与曹菊英发生争吵,用木棍将曹菊英打昏,然后致其窒息死亡并抛尸粪坑。原一审判决显示,李建功对检察机关指控其犯故意杀人罪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无异议,请求宽大处理。
2008年7月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建功死缓。2008年11月7日,新疆高院做出裁定,维持原判。
多年申诉获无罪
进入监狱服刑后,李建功开始申诉,他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2016年5月27日,王誓华律师接受李建功妹妹李翠红的委托,免费为李建功提供申诉代理服务。
经过阅卷之后,王誓华发现,该案疑点重重。“没有作案工具,也无任何能够锁定李建功杀人的客观证据,就连封在被害人口鼻处的胶带上,也未检出李建功的指纹。”王誓华告诉新京报记者。
王誓华提到,库尔勒公安局刑警大队出具的《关于李建功杀人案作案工具的搜查、检查情况说明》提到,警方按照李建功的口供,寻找作案工具和受害人的遗物,均未找到。“这说明,本案连一个可以作为旁证的物证都没有。”王誓华说。
另外,此案中死者的死亡时间、地点以及作案细节存疑。法医鉴定曹菊英死亡时间考虑在尸检前48小时左右,死亡时间段考虑在2007年12月1日14时至16时。但在2017年,北京京城明鉴法医学研究院对曹菊英的死亡时间进行再次论证。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庄洪胜主任法医师等5位专家根据此前的法医鉴定书,从角膜混浊、尸斑、尸僵以及尸绿等常用指标分析,认为曹菊英死亡时间可发生于尸检前24小时左右。王誓华认为,如果死者的死亡时间都不准确,此案便无法成立。
2018年12月6日,新疆高院认为此案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撤销原判,发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院重新审理。
2019年11月24日,此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院再审开庭。庭上,李建功19份有罪供述,全被当庭确认为非法取证,予以排除。“这样一来,全案就没有指向李建功的任何证据。”11月25日,新京报记者从参与旁听的一名人士处证实此事。
昨日,入狱近12年的李建功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

再审判决书。受访者供图
对话李建功:认罪不是我本意
身陷囹圄12年,终获无罪,李建功没有太过喜悦。“无故遭受这场灾难,(使)我没尽到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死缓判决下达后,妻子就和我离了婚。”
“作有罪供述并非本意”
新京报:你被抓的时候是什么情景?
李建功:我记得那天下午3点左右,我从菜市场买完面粉和油,刚走到家门口,四个警察拦住了我,说要带我去一趟派出所。我当时在棉纺厂工作,下午6点要去赶晚班,担心来不及,就问什么事情,结果警察猛地扑过来,将我押到警车上。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反问说,“你自己不清楚吗?”
警车一路开到了派出所,我的身体被控制着,内心特别疑惑。后来,他们说我杀了曹菊英。
新京报:你认识曹菊英吗?
李建功:我们是前后邻居,隔得不远。那时,老太太一个人住,老伴死得早,儿子们都在外工作。我们邻里关系都很和睦,她对我们挺客气的,我们从来没吵过架。实际上,我每天上班,早出晚归,很少见到她。
新京报:指控你杀人,你是什么想法?
李建功:我没做过,一直对他们说,不是我干的。但警方就认为是我干的,我说不过他们那么多人,没有一点办法。当时邻居们都说,“不是建功干的”。其中,有一个老大爷为我愤愤不平,直接气病了。
我所有亲人被挨个审讯了一遍,14岁的大女儿也被问话了,但她坚信我不会杀人。我的女儿们和我感情特别好,后来一到监狱看我,就哭着黏我。以前上学都是我骑车去送,刚被抓时,她们哭着不让我老婆送,就要爸爸。
新京报:你后来为什么作出有罪供述?
李建功:这不是我的本意。(注:再审开庭时,李建功的全部19份有罪供述,被当庭确认系非法取证,予以排除)
新京报:当时你的家庭状况如何?
李建功:我和妻子、两个女儿生活得美满幸福。当时,妻子也在棉纺厂帮工,大女儿刚满14岁,小女儿4岁。我们一家四口每月的收入2000元左右,不愁吃穿。
我被抓后,妻子一边拉扯孩子长大,一边挣钱。那正是她们最需要我挣钱养家的时候,由于无故遭受这场灾难,我没尽到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我很痛苦。后来死缓判决下达后,妻子就和我离了婚。
“我撕掉了判决书,扔进马桶”
新京报:一审判处死缓,你是怎么想的?
李建功:难受、绝望。我不明白,为什么认定是我干的。如果不是老爹、老娘还有妹妹的支持,我就不想活了。我看见判决书就生气,干脆撕了扔进马桶冲掉。
我是半文盲,小学没毕业,不认得几个字,花了很长时间写了一封申诉信,但是没人帮我寄出去。后来家属会见时,我交给了妹妹,她寄给了最高法信访办。
新京报:你在申诉时有没有放弃过?
李建功: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甚至想好了,不管多少年,服完刑出来我就继续申诉,直到获得清白。在监狱里第一次见家人时,我告诉他们,我没有杀人。老爹、老娘为了我,卖掉地和房子,倾家荡产为此奔波。大妹妹出钱,小妹妹负责跑申诉。一开始,家人给我请了好几个律师,但中途他们都放弃我了。后来请了王律师,他一直坚持帮我申诉,我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和律师。
新京报:在监狱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李建功:早晨8点起床,简单洗漱就开始干活。一般听安排,大多是些手工活。我每天都在削辣椒,小辣椒20多公斤,大辣椒15公斤,还有人做假发,通常下午5点多收工。以前还让我们去种地,后来怕逃跑,就不让出去了。
每周我们被允许看几次电视,但是我没有兴趣。干完活,我就在沙发上傻坐,想自己的事儿。我无法释怀,脑子里不停想,我是冤枉的。我既不喜欢对别人说我的案子,也不问别人的案子,我觉得没有用。我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我。有一次我说过我是冤枉的,别人说我是胡说八道。
在监狱里,我的身体也不好。腿疼,手没法伸直,眼睛看东西也像隔了层玻璃。我定期去狱医那里拿药,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好。
新京报:你在监狱里减过刑吗?
李建功:减了四次刑:死缓、无期、有期、最后减到19年2个月。表现好就能减刑。我努力干活,也不和人争吵,所以减的次数多。
“12年前,手机拨号还是按键的”
新京报:再审宣判无罪时,你是什么心情?
李建功:心里高兴、激动。我终于能和家人团聚了。现在我爹娘身体也不太好,他们天天盼我回家。这12年以来,我最大的愿望是早点回家,与他们团聚。
新京报:家人有什么变化?
李建功:爹娘老得、瘦得不成样子了。他们以前身体很好的。从再审开庭的那天起,我爹他天天趴在阳台上,看我有没有回来。我的两个妹妹也老了,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就研究我的案子。我作为长子,不在家里孝顺老人,抚养孩子,一辈子都愧对他们。
新京报:是不是还不太适应外面的社会?
李建功:是的,世界变化真快啊,我也不会用手机了。12年前,手机拨号还是按键的,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打电话。外面的街道变化很大,以前记得的地方,现在都找不到了,房子也拆了很多。出来后,我洗了个澡,和亲人们吃了一顿团聚饭,又在律师的陪同下,去监狱办理释放证。
我是真的自由了,但我现在没家了,什么都没有了。以前我的生活多好啊,现在全没了。从监狱回来后,我住在妹妹家,好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
新京报:如今再审改判无罪了,以后有什么打算?
李建功:还没有想呢。以后我们会提起国家赔偿,要求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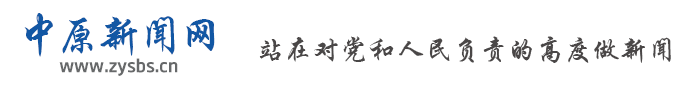
 0310-3111082
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30477986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