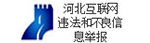豫北平原的秋天在我印象里是最为漫长的季节——收了麦子开始,一直到朔风起,霜雪降。
这期间,好多希望有了结果;好多努力有了结果;好多心中有了新的目标、新的希望。
收麦前就要育好稻秧。麦粒归仓后,接着就是犁耙整地栽水稻。
老家用的是人民胜利渠引来的黄河水,渠首还有毛主席的题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人民胜利渠(建设时称“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新中国引黄灌溉第一渠”,它的建成结束了“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的历史,揭开了开发利用黄河水沙资源的序幕。1951年3月开工修建,1952年3月第一期工程即渠首闸建成,同年4月举行开闸放水典礼。
放水了,不管白天黑夜都会有人大喊着一起往地里赶,在自己承包地头挖开个口儿,就那么坐在地头抽烟、聊天、等。
浇地有规矩,是得从上游依次而下的,一般不能插队,除非上面那一家今年不种水田,改种旱作物了。不然即使那家人不在,也会有人帮他挖开口儿,浇罢再堵好。
那时候姥姥家和俺家都种水稻。插秧很是个体力活,当然也得心灵手巧——在没膝的水中泥里背朝着焦阳眼望着自己的倒影手也不能停……直一下腰就是很好的享受了。
每次享受直腰的时候,总看见邻地的农人还在不停地运苗、分苗、插秧。看的次数多了,便产生一种羞愧出来,便也强忍着不直腰。不久,那酸痛便又击败了自尊——那几年我在上学,从初中到高中,每到这个季节,总有十几甚至更多的同学到我家和姥姥家帮我们插秧,这使得没有什么劳力的我们两家每年都能顺利按时栽上稻子,不至于落得像姥爷说的那样:人哄地一晌,地哄人一季。同时也使得我们的同窗情谊中有了特殊的成分。
插了秧,撒上肥,续了水,就等它长吧,中间遇到病虫害再打几遍药,就一直等到国庆节时的秋收了。也有种玉米、大豆、高粱、棉花、芝麻等等的,那又是一番景象。
收稻子的时候,原来是用镰刀割,捆成两把粗的捆儿,装到牲口车上运出地到场上或家门口,垛成垛,等到歇过劲儿或者借到打稻机使再脱粒。遇到连阴雨,就一捆一捆地背出稻田,装车运走,那种辛苦不可言喻。有一年甚至因为路滑,弟和我开的拖拉机翻到河里,又得从水里捞……后来有了俗称“小坦克”的联合收稻机,就像收麦子那样省劲儿了。
秋季长,因此跟姥爷姥姥相处的时间就长,记忆的东西也就多。现在他们都去世了,梦里还常出现姥爷七十多岁背着喷雾器在稻田打药、姥姥踮着小脚走在田埂上挎着篮子给我们送水送吃的、月明星高的夜晚跟邻居一块儿在地里搭的窝棚里看稻子、晚年患了病的姥姥一门心思地想往地里去……
平原的秋大多时候是一派金黄,在我看来却是很丰富的颜色。在那里,既有丰收的金黄,也有温馨的淡蓝;既有热烈的深红,也有闲逸的浅绿;既有欢快的明橙,也有深沉冷峻的黢黑......
在农村,秋季的收入远比夏收要多,若遇丰年,便可以过一个很是温暖幸福和谐的春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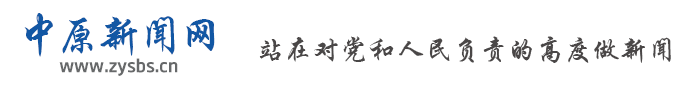
 0310-3111082
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3047798688@qq.com